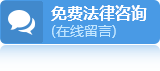商标合理使用的概念内涵与运行机理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5期 作者:周俊强,王曙光 时间:2015-03-17 阅读数:
作 为一个法学术语,合理使用(foir use)源于著作权理论;并且,在谈到合理使用时如不加说明,一般都认为是指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布莱克法律词典》的“合理使用”词条直接将其界定为: “不经作者许可,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所作的一种合理、有限的使用。”{1}从本质上看,“合理使用是依据法定因素对侵权指控的一种抗辩事由。”{2}可以 认为,合理使用既为权利人设定了依法保护自己权利、寻求侵权救济的明确范围,又给他人提供了正当利用信息资源、免受侵权追究的抗辩事由。就此而言,合理使 用理论在商标法领域内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商标领域的合理使用,在概念内涵上还没形成一致认识;在运行机理上亦需深入研究把握。
—、绪论
有论者提出,商标合理使用分为非商业性合理使用与商业性合理使用{3}。前者如,介绍、评论和研究中的合理使用,字典或类似的工具书中的合理使用 {4},执行公务中的合理使用等{5};后者又分为“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
本文认为,所谓“非商业性合理使用”不能属于商标合理使用,因为这种使用是对商标进行“作品性使用”{6},不属于“在相同或类似地商品上,使用他人 相同或近似的注册商标”的情况,不构成商标侵权,也就无须对其侵权指控设定抗辩事由。而“商业性合理使用”的提法也不准确,因为从逻辑上看“作品性使用” 也不能完全排除商业性。由于“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都是使用在商品或服务上,以商品或服务的营销为目的,因而本文倾向将这两类合理使用称为“营销性合理使用”。故此,本文对商标合理使用的探讨是就 “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即“营销性合理使用”而言的。
根据合理使用的法理内涵,本文将商标合理使用的概念界定为:为了说明自己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事实,便于消费者辨认,而对他人商标信息依法不经许 可的使用。由于商标标志的构成要素多样、商标信息的涉及范围较大,商标领域合理使用的适用对象与构成要件的确定是正确把握商标合理使用理论的关键。
二、“Classic Fair Use”的产生与成立要件
商标合理使用理论产生于美国,通过数十年的实践美国商标合理使用理论已经较为成熟。最早出现的商标合理使用被称为“Classic Fair Use”,它是在美国的《兰哈姆法》(Lanham Act)中作为对商标侵权的抗辩事由而提出的。
(一)《兰哈姆法》:“Classic Fair Use”的产生
作为一项对商标侵权指控的抗辩事由,美国1946年的《兰哈姆法》第33条(b)(4)规定{7},下列情况可以作为商标侵权指控的抗辩理由:被指控 为侵权的名称、短语或图形的使用,并非作为商标,而是(1)作为该当事人在其商业上的个人名称来使用;(2)作为与该当事人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任何人的个人 名称的使用;(3)用该名称或者图形来描述性地、合理地、善意地说明该当事人的商品或者服务本身,或者其原产地。上述内容被认为是商标合理使用的最早立法 规定,也被称为“Classic Fair Use”(我国学者一般将其翻译为“法定合理使用”或“传统合理使用”{8}。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得出,采用“Classic Fair Use”抗辩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不是作为商标或服务标志的使用;第二,属于正当和善意的使用;第三,仅仅是描述性的使用。”{9}
可以看出,《兰哈姆法》为“Classic Fair Use”设定的首要条件,即为“非商标性的使用”(otherwise than as a mark),就此而言,“Classic Fair Use”并非真正是对“商标”的合理使用。对此,台湾学者也指出,“凡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或其商品或服务之名称、形状、品质、功用、 产地或其他有关商品或服务本身之说明,非为商标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标权之效力所拘束。”{10}
应当注意,《兰哈姆法》的此项规定,隐含了深层次的商标运行机理。“Classic Fair Use”是利用他人的商标标志来描述自己的商品,其原因在于此类商标标志含有公有领域的描述性信息。因此,“Classic Fair Use”在本质上并非是对他人商标的使用,而是对他人商标标志中含有的公有领域内的描述性信息的使用,而当“承认商标权的代价主要是把一些文字从我们的语 言中除去了”{11}之时,就应当启用“Classic Fair Use”了。
(二)“持久美容”案对:混淆可能性的认识
在《兰哈姆法》法提出{12}后,通过一系列案件的适用,“Classic Fair Use”理论逐渐得到了完善。这些案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持久美容”案。
此案中的双方当事人都是美国持久美容行业的直接竞争者。持久美容是通过皮下注射液态色素混合剂,以达到增饰眼线、延长眉影、掩饰疤痕的化妆效果。持久 美容还可以用于医治色素紊乱(pigmentary disorder),故而兼具美容与治疗效果。由于这种美容措施非常方便,一次美容所形成的效果(增饰眼线、延长眉影、掩饰疤痕等),一般都能够维持3年 左右,故被称为持久(Permanent,Lasting)美容。由于持久美容与纹身类似,都是通过皮下植入色素的方式来达到改变皮肤颜色的目的,因此, 持久美容方法又被称为“纹色法”(micropigmentation)。这种美容的关键产品就是皮下注射所谓的液态色素,这种色素产品有多种颜色,瓶装 销售给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使用。
本案双方都生产用于持久美容的色素,也都已经使用“微彩”(micro color)这一词语(表现形式有微小差别,如作为一个,或两个单词,单数或复数),来宣传和销售自己的色素产品,并且其色素产品的终端使用者也是相同的,如美容沙龙。
1992年4月,本案原告Lasting Impression Inc.(简称Lasting)开始将“Micro Colors”(微彩)作为商标使用在其持久美容色素产品上,此后又将根据15 U. S. C.§1051,将包含词组“Micro Colors”(微彩)的商标向联邦专利商标局(USPT0)申请注册,1993年5月11日获得批准,注册号为Reg. No.1,769,592。该商标是黑色立体方块中的白色标准字母表现的“Micro Colors”标志,“Micro”在上“Colors”在下,中间用绿条分开。1999年,根据15 U. S. C.§1065,该商标获得无可置疑注册。{13}
本案被告 KP Permanent Make - Up, Inc.(简称 KP)提供证据证明,自从1990年起KP就已经开始在其广告插页中使用单个单词形式的“微彩”(microcolor),并且自1991起开始在其色素 瓶子上使用该标志。KP在其色素的标签上使用“microcolor”一词的方式是在瓶中色素的实际颜色标注之前,使用全部大写字母组成的 “microcolor”标志,例如:“MICROCOLOR: BLACK.”1999年(Lasting取得无可置疑注册的同一年),KP开始在其印制的10页广告册中用大号标准字体使用“microcolor”— 词。2001年1月,Lasting 发函给 KP,称其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自己的商标,已经侵犯了自己的商标权,要求KP立即停止并终止(cease and desist letters)使用该词。为了获得继续使用该词的权利,2001年3月,KP在加利福尼亚中区法院(简称“地区法院”)对Lasting提起确认之诉, 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其没有对Lasting的商标权进行侵犯,并继续有权使用“microcolor”一词。Lasting随即提起反诉,请求法院认定被告 擅自使用其注册商标构成侵权,判令KP停止使用“microcolor”一词。KP反驳认为,根据15 U.S. C.§1115(b)(4)关于合理使用的法定积极抗辩规定,其使用“microcolor”一词的行为属于“Classic Fair Use”,没有侵犯原告的商标权,并申请法院采用简易审判。
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KP对“microcolor”这一字眼的使用,是合理(fairly)和善意(in good faith)的,因为无可争议的事实表明,KP在Lasting采用“micro color”及其复数变体形式作为商标之前,就已经连续性地使用“microcolor”—词。据此,地区法院没有再审查事实上是否可能导致混淆,认定 KP已经完成其根据15U. S. C.§1115(b)(4)所作的积极抗辩,并且对KP对Lasting的侵权主张之诉进行简易审判,宣告Lasting对“microcolor”—词 不享有排他权。
Lasting不服地区法院的裁决,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简称“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审理认为{14},在消费者的任何混淆存在可能的 地方,合理使用不能认定。虽然上诉法院没有明确指出举证责任的分担,显然可以看出是将不对消费者构成混淆的举证责任交给KP来承担。上诉法院指出:KP只 在消费者对其使用的“microcolor”单词与Lasting的商标不产生混淆的可能的情况下,才能利用合理使用抗辩;而且,地区法院不对一方的消费 者关于KP商标的可能混淆进行审查,就对合理使用作出裁判,也是错误的。这样,由于在巡回上诉法院关于认定混淆的可能性的“九要素检测”(eight -factor test)中,对关键性的事实存在争议,法院推翻了简易判决。
2004年10月5日,被告KP不服上诉法院的判决,将此案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简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在商标侵权指控中提起合 理使用积极抗辩时,没有责任承担否认消费者对涉案产品或服务产生混淆的可能的举证责任。最高法院认为,虽然消费者混淆也许在评估被告的使用是否客观合理具 有意义。然而,对照《兰哈姆法》的相关条款,最高法院发现该法将证明混淆的可能的责任赋予侵权指控方,并且没有就混淆的可能问题,对合理使用抗辩成立要素 提出任何要求。据此,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判决认为“Likehood of Confusion”与“Classic Fair Use”可以并存,即使在“Likehood of Confusion”存在的情况下,“Classic Fair Use”抗辩仍然可能成立。
最高法院指出,如果原告成功地使本案成为表面证据确凿案(prima facie case){15},包括消费者混淆的可能因素,被告也可以提交反驳证据,以削弱原告关于这些因素的证据的效力,或即使在表面证据确凿案成立时,也提起积 极性抗辩以阻止侵权救济的施行,或两者都去做。因为提供混淆可能性证据的责任在原告,对主张合理使用的被告没有出示非混淆可能的独立要求。与第九巡回法院 的观点相反,最高法院法庭认为:消费者混淆的一些可能性与合理使用是可以并存的。由于最高法院并没有对合理使用抗辩所能包容的消费者混淆的程度作出相关规 定,因此,15 U. S. C.§1115(b)(4)中的“合理地使用”条件,只要求描述性词语准确地描述商品。从逻辑上看,当被告是描述性地(descriptively)、善 意地(in good faith)、非商标地(not as a mark)使用原告商标,因而提起合理使用抗辩。如果原告没能为其提出的侵权指控,完成其商标遭受混淆的可能的举证责任,任何要求提起合理使用抗辩的被告 必须承担非混淆证明责任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三、“Nominative Fair Use”的创设与适用
《兰哈姆法》规定的合理使用,仅限于非商标性的描述性使用。但是,由于商标本身携带了关于产品及其来源的事实信息,在商业实践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 况,他人的商标与自己经营的商品或服务存在某种事实上的关联,只有使用他人的商标才能让消费者获得自己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事实信息。为了弥补《兰哈姆法》 合理使用的上述不足,在美国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确认了另一种形式的合理使用,即“Nominative Fair Use”(我国学者一般将其翻译为“被提及合理使用”或“指明商标权人的合理使用”{16}。)
(一)“街边新仔”案:“Nominative Fair Use”的创设
这种形式的合理使用是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审理“New kids On The Block v. News America Publishing, Inc.”{17}
该案中,“New Kids On The Block”(街边新仔)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商标。原告“街边新仔”组合乐队1985年成立于波士顿,出道一年即风靡全美。案卷显示,当时“街边新仔”商标 已经使用于500个以上的产品或服务。在这些服务中包括“900电话”业务,“粉丝”们只要向电话机中投入钱币,就可以通过拨打不同的900号码来聆听 “街边新仔”之间的谈话,也可以听到其他“粉丝”关于“街边新仔”的交谈,或者向“新街边仔”或其他“粉丝”发送短信。该案的被告是美国新闻出版公司 (News America Publishing)和甘尼特卫星信息网络公司(Gannett Satellite Information Network,Inc.),他们分别出版 The USA Today 和 The Star两份报纸,也经营各自的“900电话”业务。两被告在各自报纸上发起了一项评选活动,请读者通过拨打“900电话”(每次缴费50美分),评选出 自己心目中最性感、最喜欢的“New Kid”。为此,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New Kids On.The Block”乐队五人组合的照片,并使用了“New Kids On The Block”商标。同时还在在报纸上公布了评选专线的“900电话”号码。原告由此提起诉讼,认为被告宣传中擅自使用了其商标,构成了商标侵权。初审法院 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被告的相关言论自由权利而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原告不服,遂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Classic Fair Use”是利用他人的商标标志中含有的公有领域内的描述性信息来描述自己的商标或服务,而不是指向原告的商品或服务。但是,本案中被告使用原告的商标来描 述原告的,而不是被告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即被告并没有利用原告的商标来描述被告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被告使用“街边新仔”商标是用来指向“街边新仔”本身 的,因此本案被告对原告商标的使用不属于“Classic Fair Use”。
为此,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突破了“Classic Fair Use”的原有框架,创设了与“Classic Fair Use”并行的“Nominative Fair Use”理论。“Nominative Fair Use”适用于被告使用原告的商标去指向原告的产品,虽然被告的最终目的还是描述自己的产品;相反地,“Classic Fair Use”适用于被告用原告的商标仅仅去描述自己的产品,根本不去指向原告的产品。相应地,“Nominative Fair Use”必须同时满足下列三项条件:“第一,如果不使用他人的商标,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将难以描述;第二,商标的使用必须限制在适度与必须的范围内;第三, 使用者不能进行任何关于得到商标持有人赞助或支持暗示的行为。”{18}从本质上看,这三项条件分别从使用的必要性、使用的适度性以及使用的非暗示性这三 个方面,为“Nominative Fair Use”规定主观和客观限制。
依照上述条件,上诉法院对本案分析如下:首先,使用的必要性。事实上,人们在不熟悉“街边新仔”的名称时无法谈论这个组合乐队。因 此,“Nominative Fair Use”的第一个条件是符合的。其次,使用的适度性。报纸广告对“新街边仔”商标的使用是在说明民意测验内容的必要程度内,并且没有在此范围外使用的区别 性标志或者“新街边仔”的任何其他信息。因此,“Nominative Fair Use”的第二个条件也符合。最后,使用的非暗示性。本案中,两份报纸广告没有进行任何获得“新街边仔”赞助或支持的暗示。The USA Today甚至还向读者提出了“the New Kids”是否会走下坡路的问题,这恰恰表明了与赞助或支持相反的关系。显然,“Nominative Fair Use”的第三个条件也是满足的。
应当指出,“Nominative Fair Use”的提出,不但解决了为了说明自己与他人的经营项目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情况下对他人商标的合理使用问题,同时为该种合理使用的成立设定了与 “Classic Fair Use”不同的要件。这样,通过“街边新仔”案的审理,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创设了与“Classic Fair Use”并行的“Nominative Fair Use”理论,提出了判定“Nominative Fair Use”抗辩的三要件,从而标志了商标合理使用理论在整体上的形成。由此,“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一起,构成了商标合理使用理论的基本框架。
(二)“海滩男孩”案:对两类合理使用的区分
商标合理使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以后,在实践中却遇到了难以区别适用问题。例如,在2002年的“花花公子”案中{19},加利福利亚地区法院认为被 告对原告商标的使用既属于“Classic Fair Use”又属于“Nominative Fair Use”。这种将两种形式商标合理使用不加区分地适用的做法,在理论上淡化了两类合理使用的区分意义,实践上混淆了两类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直到2003 年“海滩男孩”案{20}一案中确立的。的判决,才从根本上分清了两类合理使用的适用对象。
此案中,“海滩男孩”(Beach Boys)是一个乐队的名称,该乐队是1961年由包括A1 Jardine与Mike Love在内的五人创建。乐队成立后,创作了很多畅销歌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在全美拥有众多听众。1967年,“Beach Boys”成员组建了“Brothers Records, Inc.”(简称 BRI)以持有和管理“Beach Boys”名下的知识产权。数年之后,Jardine 与Love不再参加共同巡演,并分别组建了自己的乐队。Love乐队获得BRI授权使用“The Beach Boys”商标。Jardine也试图获得该项授权,但因其条件不符合BRI的要求而被拒绝。此后,Jardine的乐队继续使用包含“Beach Boys”商标的乐队名称进行演出。由于两个乐队都以“The Beach Boys”或近似的名义巡演,演出组织者在预订了Jardine的乐队后,有时弄不清到底是哪支乐队会来。很多观看过Jardine表演的人也抱怨,他们 搞不清到底是谁在表演。1999年4月9日,BRI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主张Jardine侵犯
其商标权。地区法院最终作出了支持原告的初审判决,Jardine对此判决不服,于2002年12月上诉于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在上诉审中,Jardine坚持认为他对BRI商标的使用既属于“Classic Fair Use”又属于“Nominative Fair Use”,并根据上诉法院在“New Kids”案中提出的区分两类合理能够得标准提出:第一,他使用“The Beach Boys”商标来描述“Beach Boys”的产品,因此应当适用“Nominative Fair Use”分析;第二,作为另一选择,他使用“The Beach Boys”商标只描述他自己—— Beach Boys的创始成员——根本没有描述Beach Boys的产品,据此又应当适用“Classic Fair Use”分析。
针对Jardine的抛出的难题,上诉法院另辟蹊径,从商标的两层含义的角度指出:Jardine没有使用“The Beach Boys”商标来表示它第一层的描述性含义,即“常去海边沙滩的男孩”。反而,Jardine是在第二层含义,即商标的意义上,使用“The Beach Boys”商标,也就是在表示这个乐队——它的成员——流行的加尼福利亚冲浪文化(popularized California surfing culture)。事实上,无论Jardine使用该商标指向他自己,还是他的乐队,就是因为Jardine没有在该标志的第一层描述性意义上使用,所以 不能适用“Classic Fair Use”。
这样,本案只能在“Nominative Fair Use”的范围内进行。最后,上诉法院对照在“街边新仔”一案确定的“Nominative Fair Use”抗辩的三个条件,认为Jardine对“The Beach Boys”商标的使用,暗示受到了商标持有人的赞助或者支持,没能满足“Nominative Fair Use”的“非暗示性使用”要件,最后判定Jardine败诉。
本案的判决在商标合理使用理论发展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两类合理使用的适用判定的判定上。在“街边新仔”案中,法院将“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进行区别的依据是“使用目的”的不同,前者是为了描述使用者自己的商品,而后者是为了指向商标权利人的商品。然而,这种“使用目的标准”在使用者 本身与商标权利人或其商标或服务有事实上的关联的时候,如本案中的Jardine与“Beach Boys”乐队,由于使用者对商标的使用兼有两种目的,因此也就无法再对两类合理使用进行区分。本案中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使用目的标准”无法区 分两类合理使用的情况下,突破原有的理论,向前跨出了具有的重要意义的一步,提出了“使用信息标准”,从而彻底解决了“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的适用问题,这是对合理使用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另外本案的判决对“Nominative Fair Use”构成要件的运用也有实际意义。“街边新仔”案的判决给出了“Nominative Fair Use”的三要件,即必要性、适度性与非暗示性。应当指出,这三个要件的提出是以“Nominative Fair Use”为对象的,因此也都是从使用行为本身而言的,即使用的必要性、使用的适度性与使用的非暗示性。有人认为,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本案中将被 告使用行为的“非暗示性”要件转化为消费者感觉的“非混淆性”要件。对此,下文将给予深入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认识。
四、商标合理使用的本质与运行机理
知识产权的价值在于使用而非占有,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也就是对知识产权利用的保护。从整体上来看,对商标的使用是对商标荷载的信息的使用,而由于商标的信息构成较为复杂,对商标中不同层次信息的利用其性质与后果也是不同的。
(一)“第一含义合理使用”与“第二含义合理使用”
总的说来,任何一件商标标志都包含两个层次的信息:第一,商标标志本身所具有的一般意义信息,如苹果标志之于一种水果;第二,商标标志本身与特定商品 关联所荷载的特定商品信息,如苹果标志之于一种手机。在商标法领域,前者被称为商标标志的第一含义,后者即为商标标志的第二含义。可以认为,一个标志或符 号只有当其与特定的商品进行关联,荷载了该特定商品的信息以后才能成为商标;只有第一含义的标志不能成为商标,而只对第一含义信息的利用也就不构成对商标 的使用。正是有基于此,美国的《兰哈姆法》才对其第33条(b)(4)所规定的抗辩事由称为非商标性使用(otherwise than as a mark)。
在“街边新仔”案中,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现被告使用“街边新仔”商标之目的是用来指向“街边新仔”本身而不是被告自己的商品,认为本案被告对 原告商标的使用不属于“Classic Fair Use”,从而确认了“Nominative Fair Use”抗辩。然而,由于这种“使用目的标准”没有在本质上反映商标合理使用的运行机理,这也为后来在两类合理使用抗辩的适用问题上埋下隐患。直到 Jardine在“海滩男孩”一案中的发难,才“逼使”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不得不彻底放弃其所建立的“使用目的标准”,而另辟“使用信息标准” {21},这样才从根本上解决了两类合理使用抗辩的适用问题。
从本质上看,商标合理使用的运行机理在于对商标标志所荷载的不同层次信息的利用:“Classic Fair Use”是对商标标志第一含义的使用,而“Nominative Fair Use”则是在第二含义的意义上对商标标志的使用。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对“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这对商标合理使用术语的翻译一般有三个角度:第一,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如将“Classic Fair Use”译为“传统合理使用”,将“Nominative Fair Use”译为“被提及合理使用”;第二,按照法律依据翻译,如将“Classic Fair Use”译为“法定合理使用”;第三,按照“使用目的标准”翻译,如将“Classic Fair Use”译为“描述性合理使用”,将“Nominative Fair Use”译为“指示性合理使用”或“指明商标权人的合理使用”。这些译法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翻译对象的内涵,都可谓译之有据。只是,基于对商标合理使用运 行机理的认知,本文认为对这两类商标合理使用的术语,应当以“使用信息标准”为依据,分别翻译为“第一含义合理使用(Fair Use of First Meaning, FUFM)”和“第二含义合理使用(Fair Use of Secend Meaning, FUSM)”,如此不但能说明这两类合理使用的本质,同时也从内涵上阐明了这两类合理使用的区别。
(二)混淆的可能性与两类合理使用的成立
非混淆性,是商标存在的基本价值,也是商标保护的基本目标。毋庸置疑,对非混淆性的态度,也是正确理解与掌握商标合理使用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
1.第一含义合理使用与混淆的可能性。前文论及,第一含义合理使用在本质上并非是对他人商标的使用,而是对他人商标标志中含有的公有领域内的描述性信 息的利用。由于这些公有领域内的信息,并不能因为被作为特定商标标志而完全私有化,其公有性不会因此而失去;所以他人在公有信息领域内,即在第一含义层面 上对商标标志的利用,当不受商标权人的控制。这也是第一含义合理使用存在的法理基础。就商标权人言之,他通过赋予公有领域内的信息第二含义,从而完成一个 完整的商标“制造”过程。然而,公有领域内的信息——商标标志的第一含义,不但不会因为商标权的存在而被私有;相反,私有领域内的信息—商标标志的第二含 义,则应为其对公有领域内信息的利用而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就是商标标志的第二含义,因其对商标标志的第一含义的关联,而应当忍受他人在利用公有 领域内第一含义信息时,有可能造成的与第二含义的混淆。正是基于上述认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持久美容”案中认为:消费者混淆的一些可能性与合理使用是 可以并存的。当然,这里的并存也并非没有限度,合理使用对混淆的可能性的容忍不能突破第一含义合理使用的第二个要件,即“正当和善意”的范围。换言之,混 淆的可能性对第一含义合理使用抗辩是否成立的作用不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通过正当与善意要件来实现。
由于对此问题的认识没有到位,我国一些法院在审理第一含义合理使用相关案件时,没能把握问题的核心。例如,在“联友卤制品厂诉柏代娣”一案中 {22},被告对原告商标的使用显然不能适用第二含义合理使用分析,而应采用第一含义合理使用分析。尽管本案的一审与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相反,但均将作为 事实问题的“混淆与误认”当成判决的依据,而不是以作为法律问题的“正当与善意”作为分析的核心,以致一审法院因“被告柏代娣在同类商品上突出使用‘茅 山’字样”而判定其侵权;二审法院又是首先认定“‘茅山’二字是因地而知名,不是因商标而知名”等问题。事实上,对于第一含义合理使用的抗辩,无论使用者 如何“突出”使用包含在他人商标中词语,也无论该词语是否“知名”都不妨碍其抗辩的成立。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在该词语的第一含义上,正当、善意地使用。
2.第二含义合理使用与混淆的可能性。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的包括非暗示性在内的,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这三个要件,是从使用行为本身的性质来 要求,而非从一般消费者感觉的角度来判断的。当原告通过证明混淆可能的存在,而支持其侵权指控时,由于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设立,使得被告不必再承担证明非 混淆可能的责任,就可对原告的侵权指控进行抗辩。{23}然而,该理论随着1992年“街边新仔”案的判决而确立以后,却遭致了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有学 者就认为:“用第二含义合理使用抗辩取代混淆可能性分析,这貌似有益的做法却严重背离了商标法的原则”。{2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产生了混淆的可 能,那么有可能是被告的暗示,还有可能是比暗示更严重的明示。就此而言,非暗示性要求比混淆的可能要求更加严格。这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街边新 仔”一案中确立的第二含义合理使用,是在商标侵权指控中为被告提供的一项免责事由,而不是对被告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也就没有第二含义合理使用存在的必 要。
到了2003年的“海滩男孩”一案,法院不再强调非暗示性本身的分析,而是证明Jardine行为在消费者中造成的混淆,来证明Jardine对 BRI商标大使用没有满足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三个条件。这实际上也就给人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第三个条件由原来的非暗示性,变成了非混 淆性。问题是,如果被告能够证明自己对原告商标的使用并没有在消费者中造成混淆,那还用得着所谓的合理使用抗辩吗?况且,“在街边新仔一案中为了帮助被告 而确认的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唯一不同是,比Sleek-craft增加了更繁杂的证明责任。换言之,对被告来说 Sleekcraft test比Jardine版的第二含义合理使用更加容易达到。”{25}有基于此,有学者断言:“为了和商标法取得一致的对此原则的拯救的实际效果,第九 巡回法院通过采用额外的检测无形中放弃了第二含义合理使用。”{26}
本文认为,如果说第一含义合理使用是在公共大道上行走,那么第二含义合理使用则已进入私有土地了。因此,第二含义合理使用抗辩成立的前提就是“使用的 必要性”,也即非此而无其他办法,就如同相邻权中只有经过他人土地,否则无法出入一样。虽然,基于“使用的必要性”,法律允许他人对商标第二含义信息进行 有限的使用;但是,由于是对他人纯粹私人权利的利用,那么这种利用就不可能不影响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在深入分析这种使用的性质之前,考察一下物权法对相 邻权性质的认定至为重要。
物权法关于相邻权的界定,通说为:“相邻权亦称相邻关系,谓相邻接不动产之所有人间,一方所有人之自由支配力与他方所有人之自由排他力相互冲突时,为 调和其冲突,以谋共同之利益,以法律规定直接所人权利之总称。故相邻权为所有权之限制或扩大。”{27}“所谓相邻关系是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所有人 或占有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时,相互之间应当给予便利或者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28}“相邻关系依存于相邻不动产的 所有权关系或使用关系,其实质是相邻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扩张或限制。”{29}上述关于相邻权或相邻关系性质的表述虽然不尽一致,但都认为相邻权或相 邻关系,在本质上是相邻不动产各方权利人的相关权利的限制与扩张关系。之所以产生这种限制与扩张关系,“盖不动产既系位置固定不移之物,而天下之不动产又 不能尽归一人所独有,则甲之不动产与乙之不动产,势必结邻,加以居今之世,又非古人所谓‘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因而相邻间彼此权 利之行使,即难免发生冲突,此种冲突若不解决,则直接影响于所有物之完全利用者固大,间接影响于社会秩序及国民经济者亦复不小,为此法律对于各所有权之内 容,即不能不于一定之范围内加以限制,同时对于各所有权人亦不能不于一定之范围内,课以协力之义务,必能调和双方之利害,而期达到共存共荣之目的。此种所 有权有时受限制,有时得扩张之情形,即所谓相邻关系是也。”{30}“调和利害,共存共荣”,这是相邻权产生的法理基础,也是商标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正当 性依据。可见,相邻权所限制与扩张的对象,是物的利用关系,即物权法的物尽其用宗旨使然;而非物的归属关系,非物权法定份止争要求的结果。对此,日本民法 学家我妻荣先生就有精辟论述:“相邻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对‘利用’的调节,而非对‘所有’的调节。”{31}
正如相邻权的产生的客观前提是不同权利人不动产的事实邻接一样,非利用他人的不动产权利无法发挥自己不动产的效用;商标第二含义合理使用产生的客观前 提则是不同商品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的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的产品或服务与被使用商标存在事实上的关联,非使用他人商标无法准确地说明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消费 者也无从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它们在本质上都不是权利归属的重新分配,而是对权利使用的协调。对商标使用者来说,是其权利的扩张,对商标权利人来 说是其权利的限制。既然是对商标权利的限制,那么就不再依据混淆的可能标准来作为这种合理使用成立的依据,否则就是商标权的一般保护,而第二含义合理使用 意义下对商标权利的限制也就无从谈起。本文认为,这正是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街边新仔”案中,将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第三个要件设定为“非暗示”, 而不是“非混淆”的根本原因。
另外,也有必要对暗示与混淆的关系作一常分析。暗示,作为“混淆的可能性这枚硬币的一面”{32},虽然有可能导致消费者混淆或误认的后果。但是,从 性质上看,二者本质并不相同,前者是基于商标使用行为本身合理性的考量,后者则是基于消费者的认识状况的考量;从因果关系上看,二者亦无必然关联:首先, 暗示并不一定导致混淆,“你这厢暗送秋波,他那里不解风情”的情况,显然也是有的;其次,混淆也并非一定因暗示,因为混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明示会直接导 致混淆。换言之,暗示并不必然致混淆,混淆也并非一定因暗示。暗示要件的提出,完全出自使用行为本身的性质,即使用行为合理性的考量。
(责任编辑 罗刚) 【注释】
{1}Biyan A. Garner Editor in Chief, Black's Law Dictionary(Eighth Edition),2004West, a Thomson business. P.634.
{2}Bryan A. Garner Editor in Chief, Black's Law Dictionary(Eighth Edition),2004West, a Thomson business. P.634.
{3}武敏:《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初探》,载《中华商标》,2002年第7期;傅钢:《商标的合理使用及其判断标准——从〈商标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谈起》,载《电子知识产权》,2002年第12期。
{4}王迁著:《知识产权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1页。
{5}袁杏桃:《试论商标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建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4期。
{6}例如,在作品中为叙述某一情节,而使用商标。
{7}The “fair use” defense codified in section 33(b)(4) of the Lanham Act, 15 U. S. C.§1115(b)(4).
{8}如邱进前:《美国商标合理使用原则的新发展:TheBeach Boys—案评析》,载《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5期;冯晓青:《商标权的限制研究》,载《学海》2006年第4期。
{9}BLI Editorial Staff, Corporate Counsel's Guide to Trademark Law, Thomson/West, 2006. p4.071.
{10}陈樱琴、叶玟妤著:《智慧财产权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63页。
{11}Robert P. merges Peter S. Menell Mark A. Lemley Thomas M. Jor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Publishers 2007, p.712
{12}KP PERMANENT MAKE-UP, INC. v. LASTING IMPRESSION I,INC.,et al.,543 U. S.03-409(2004).
{13}“the Lanham Act”,60 Stat.427,as amended, 15 U. S. C.§1051 et seq.,规定商品或服务标志的使用者有机会向PT0寻求注册,15 U. S. C.§1051,1053.如果一项注册满足不间断连续使用5年的进一步条件,“商业使用该注册商标以表明商品来源)的权利”将在此外获得“无可置疑”注 册。
{14}328 F.3d 1061(2003).
{15}The establishment of a legally required rebuttable presumption.
{16}如杜颖:《指明商标权人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一以美国法为中心的比较分析》,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9期;武敏:《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初探》,载《中华商标》2002年第7期。
{17}New kids On The Block v. New America Publishing, Inc.971 F 2d 302(9th Cir.1992)
{18}971 F.2d 302(9th Cir.1992), P 308.
{19}Playboy Enterprises Inc. v. Terns Welles.279 F.3d 796(9th Cir.2002)
{20}Brothers Records, Inc. v. Jardine.318 F.3d 900(9th Cir.2003)
{21}这里“使用目的标准”与“使用信息标准”的提法,是本文作者根据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区分两类合理使用的不同依据所总结提出的,而非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直接提法。
{2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8期,第37页。
{23}Brothers Records, Inc. v. Jardine.318 F.3d 900(9th Cir.2003)
{24}Chad J. Doellinger, Nominative Fair Use: Jardine and the Demise of a Doctrine,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ume 1,Issue 1(Spring 2003).
{25}Chad J. Doellinger, Nominative Fair Use: Jardine and the Demise of a Doctrine,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ume 1,Issue 1(Spring 2003).
{26}Chad J. Doellinger, Nominative Fair Use : Jardine and the Demise of a Doctrine,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ume 1,Issue 1(Spring 2003).
{27}史尚宽著:《物权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本文笔者所加。
{28}法学研究编辑部:《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本文笔者所加。
{29}彭万林主编:《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本文笔者所加。
{30}郑玉波著:《民法物权》,北京:三联书局1986年版,第77页。
{31}[日]我妻荣著:《物权法(民法讲义II)》,东京:岩波书店昭和27年刊行,第185页。
{32}Jardine, 318 F.3d at 908 n.5(9th Cir.2003).
—、绪论
有论者提出,商标合理使用分为非商业性合理使用与商业性合理使用{3}。前者如,介绍、评论和研究中的合理使用,字典或类似的工具书中的合理使用 {4},执行公务中的合理使用等{5};后者又分为“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
本文认为,所谓“非商业性合理使用”不能属于商标合理使用,因为这种使用是对商标进行“作品性使用”{6},不属于“在相同或类似地商品上,使用他人 相同或近似的注册商标”的情况,不构成商标侵权,也就无须对其侵权指控设定抗辩事由。而“商业性合理使用”的提法也不准确,因为从逻辑上看“作品性使用” 也不能完全排除商业性。由于“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都是使用在商品或服务上,以商品或服务的营销为目的,因而本文倾向将这两类合理使用称为“营销性合理使用”。故此,本文对商标合理使用的探讨是就 “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即“营销性合理使用”而言的。
根据合理使用的法理内涵,本文将商标合理使用的概念界定为:为了说明自己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事实,便于消费者辨认,而对他人商标信息依法不经许 可的使用。由于商标标志的构成要素多样、商标信息的涉及范围较大,商标领域合理使用的适用对象与构成要件的确定是正确把握商标合理使用理论的关键。
二、“Classic Fair Use”的产生与成立要件
商标合理使用理论产生于美国,通过数十年的实践美国商标合理使用理论已经较为成熟。最早出现的商标合理使用被称为“Classic Fair Use”,它是在美国的《兰哈姆法》(Lanham Act)中作为对商标侵权的抗辩事由而提出的。
(一)《兰哈姆法》:“Classic Fair Use”的产生
作为一项对商标侵权指控的抗辩事由,美国1946年的《兰哈姆法》第33条(b)(4)规定{7},下列情况可以作为商标侵权指控的抗辩理由:被指控 为侵权的名称、短语或图形的使用,并非作为商标,而是(1)作为该当事人在其商业上的个人名称来使用;(2)作为与该当事人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任何人的个人 名称的使用;(3)用该名称或者图形来描述性地、合理地、善意地说明该当事人的商品或者服务本身,或者其原产地。上述内容被认为是商标合理使用的最早立法 规定,也被称为“Classic Fair Use”(我国学者一般将其翻译为“法定合理使用”或“传统合理使用”{8}。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得出,采用“Classic Fair Use”抗辩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不是作为商标或服务标志的使用;第二,属于正当和善意的使用;第三,仅仅是描述性的使用。”{9}
可以看出,《兰哈姆法》为“Classic Fair Use”设定的首要条件,即为“非商标性的使用”(otherwise than as a mark),就此而言,“Classic Fair Use”并非真正是对“商标”的合理使用。对此,台湾学者也指出,“凡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或其商品或服务之名称、形状、品质、功用、 产地或其他有关商品或服务本身之说明,非为商标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标权之效力所拘束。”{10}
应当注意,《兰哈姆法》的此项规定,隐含了深层次的商标运行机理。“Classic Fair Use”是利用他人的商标标志来描述自己的商品,其原因在于此类商标标志含有公有领域的描述性信息。因此,“Classic Fair Use”在本质上并非是对他人商标的使用,而是对他人商标标志中含有的公有领域内的描述性信息的使用,而当“承认商标权的代价主要是把一些文字从我们的语 言中除去了”{11}之时,就应当启用“Classic Fair Use”了。
(二)“持久美容”案对:混淆可能性的认识
在《兰哈姆法》法提出{12}后,通过一系列案件的适用,“Classic Fair Use”理论逐渐得到了完善。这些案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持久美容”案。
此案中的双方当事人都是美国持久美容行业的直接竞争者。持久美容是通过皮下注射液态色素混合剂,以达到增饰眼线、延长眉影、掩饰疤痕的化妆效果。持久 美容还可以用于医治色素紊乱(pigmentary disorder),故而兼具美容与治疗效果。由于这种美容措施非常方便,一次美容所形成的效果(增饰眼线、延长眉影、掩饰疤痕等),一般都能够维持3年 左右,故被称为持久(Permanent,Lasting)美容。由于持久美容与纹身类似,都是通过皮下植入色素的方式来达到改变皮肤颜色的目的,因此, 持久美容方法又被称为“纹色法”(micropigmentation)。这种美容的关键产品就是皮下注射所谓的液态色素,这种色素产品有多种颜色,瓶装 销售给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使用。
本案双方都生产用于持久美容的色素,也都已经使用“微彩”(micro color)这一词语(表现形式有微小差别,如作为一个,或两个单词,单数或复数),来宣传和销售自己的色素产品,并且其色素产品的终端使用者也是相同的,如美容沙龙。
1992年4月,本案原告Lasting Impression Inc.(简称Lasting)开始将“Micro Colors”(微彩)作为商标使用在其持久美容色素产品上,此后又将根据15 U. S. C.§1051,将包含词组“Micro Colors”(微彩)的商标向联邦专利商标局(USPT0)申请注册,1993年5月11日获得批准,注册号为Reg. No.1,769,592。该商标是黑色立体方块中的白色标准字母表现的“Micro Colors”标志,“Micro”在上“Colors”在下,中间用绿条分开。1999年,根据15 U. S. C.§1065,该商标获得无可置疑注册。{13}
本案被告 KP Permanent Make - Up, Inc.(简称 KP)提供证据证明,自从1990年起KP就已经开始在其广告插页中使用单个单词形式的“微彩”(microcolor),并且自1991起开始在其色素 瓶子上使用该标志。KP在其色素的标签上使用“microcolor”一词的方式是在瓶中色素的实际颜色标注之前,使用全部大写字母组成的 “microcolor”标志,例如:“MICROCOLOR: BLACK.”1999年(Lasting取得无可置疑注册的同一年),KP开始在其印制的10页广告册中用大号标准字体使用“microcolor”— 词。2001年1月,Lasting 发函给 KP,称其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自己的商标,已经侵犯了自己的商标权,要求KP立即停止并终止(cease and desist letters)使用该词。为了获得继续使用该词的权利,2001年3月,KP在加利福尼亚中区法院(简称“地区法院”)对Lasting提起确认之诉, 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其没有对Lasting的商标权进行侵犯,并继续有权使用“microcolor”一词。Lasting随即提起反诉,请求法院认定被告 擅自使用其注册商标构成侵权,判令KP停止使用“microcolor”一词。KP反驳认为,根据15 U.S. C.§1115(b)(4)关于合理使用的法定积极抗辩规定,其使用“microcolor”一词的行为属于“Classic Fair Use”,没有侵犯原告的商标权,并申请法院采用简易审判。
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KP对“microcolor”这一字眼的使用,是合理(fairly)和善意(in good faith)的,因为无可争议的事实表明,KP在Lasting采用“micro color”及其复数变体形式作为商标之前,就已经连续性地使用“microcolor”—词。据此,地区法院没有再审查事实上是否可能导致混淆,认定 KP已经完成其根据15U. S. C.§1115(b)(4)所作的积极抗辩,并且对KP对Lasting的侵权主张之诉进行简易审判,宣告Lasting对“microcolor”—词 不享有排他权。
Lasting不服地区法院的裁决,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简称“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审理认为{14},在消费者的任何混淆存在可能的 地方,合理使用不能认定。虽然上诉法院没有明确指出举证责任的分担,显然可以看出是将不对消费者构成混淆的举证责任交给KP来承担。上诉法院指出:KP只 在消费者对其使用的“microcolor”单词与Lasting的商标不产生混淆的可能的情况下,才能利用合理使用抗辩;而且,地区法院不对一方的消费 者关于KP商标的可能混淆进行审查,就对合理使用作出裁判,也是错误的。这样,由于在巡回上诉法院关于认定混淆的可能性的“九要素检测”(eight -factor test)中,对关键性的事实存在争议,法院推翻了简易判决。
2004年10月5日,被告KP不服上诉法院的判决,将此案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简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在商标侵权指控中提起合 理使用积极抗辩时,没有责任承担否认消费者对涉案产品或服务产生混淆的可能的举证责任。最高法院认为,虽然消费者混淆也许在评估被告的使用是否客观合理具 有意义。然而,对照《兰哈姆法》的相关条款,最高法院发现该法将证明混淆的可能的责任赋予侵权指控方,并且没有就混淆的可能问题,对合理使用抗辩成立要素 提出任何要求。据此,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判决认为“Likehood of Confusion”与“Classic Fair Use”可以并存,即使在“Likehood of Confusion”存在的情况下,“Classic Fair Use”抗辩仍然可能成立。
最高法院指出,如果原告成功地使本案成为表面证据确凿案(prima facie case){15},包括消费者混淆的可能因素,被告也可以提交反驳证据,以削弱原告关于这些因素的证据的效力,或即使在表面证据确凿案成立时,也提起积 极性抗辩以阻止侵权救济的施行,或两者都去做。因为提供混淆可能性证据的责任在原告,对主张合理使用的被告没有出示非混淆可能的独立要求。与第九巡回法院 的观点相反,最高法院法庭认为:消费者混淆的一些可能性与合理使用是可以并存的。由于最高法院并没有对合理使用抗辩所能包容的消费者混淆的程度作出相关规 定,因此,15 U. S. C.§1115(b)(4)中的“合理地使用”条件,只要求描述性词语准确地描述商品。从逻辑上看,当被告是描述性地(descriptively)、善 意地(in good faith)、非商标地(not as a mark)使用原告商标,因而提起合理使用抗辩。如果原告没能为其提出的侵权指控,完成其商标遭受混淆的可能的举证责任,任何要求提起合理使用抗辩的被告 必须承担非混淆证明责任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三、“Nominative Fair Use”的创设与适用
《兰哈姆法》规定的合理使用,仅限于非商标性的描述性使用。但是,由于商标本身携带了关于产品及其来源的事实信息,在商业实践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 况,他人的商标与自己经营的商品或服务存在某种事实上的关联,只有使用他人的商标才能让消费者获得自己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事实信息。为了弥补《兰哈姆法》 合理使用的上述不足,在美国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确认了另一种形式的合理使用,即“Nominative Fair Use”(我国学者一般将其翻译为“被提及合理使用”或“指明商标权人的合理使用”{16}。)
(一)“街边新仔”案:“Nominative Fair Use”的创设
这种形式的合理使用是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审理“New kids On The Block v. News America Publishing, Inc.”{17}
该案中,“New Kids On The Block”(街边新仔)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商标。原告“街边新仔”组合乐队1985年成立于波士顿,出道一年即风靡全美。案卷显示,当时“街边新仔”商标 已经使用于500个以上的产品或服务。在这些服务中包括“900电话”业务,“粉丝”们只要向电话机中投入钱币,就可以通过拨打不同的900号码来聆听 “街边新仔”之间的谈话,也可以听到其他“粉丝”关于“街边新仔”的交谈,或者向“新街边仔”或其他“粉丝”发送短信。该案的被告是美国新闻出版公司 (News America Publishing)和甘尼特卫星信息网络公司(Gannett Satellite Information Network,Inc.),他们分别出版 The USA Today 和 The Star两份报纸,也经营各自的“900电话”业务。两被告在各自报纸上发起了一项评选活动,请读者通过拨打“900电话”(每次缴费50美分),评选出 自己心目中最性感、最喜欢的“New Kid”。为此,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New Kids On.The Block”乐队五人组合的照片,并使用了“New Kids On The Block”商标。同时还在在报纸上公布了评选专线的“900电话”号码。原告由此提起诉讼,认为被告宣传中擅自使用了其商标,构成了商标侵权。初审法院 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被告的相关言论自由权利而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原告不服,遂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Classic Fair Use”是利用他人的商标标志中含有的公有领域内的描述性信息来描述自己的商标或服务,而不是指向原告的商品或服务。但是,本案中被告使用原告的商标来描 述原告的,而不是被告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即被告并没有利用原告的商标来描述被告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被告使用“街边新仔”商标是用来指向“街边新仔”本身 的,因此本案被告对原告商标的使用不属于“Classic Fair Use”。
为此,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突破了“Classic Fair Use”的原有框架,创设了与“Classic Fair Use”并行的“Nominative Fair Use”理论。“Nominative Fair Use”适用于被告使用原告的商标去指向原告的产品,虽然被告的最终目的还是描述自己的产品;相反地,“Classic Fair Use”适用于被告用原告的商标仅仅去描述自己的产品,根本不去指向原告的产品。相应地,“Nominative Fair Use”必须同时满足下列三项条件:“第一,如果不使用他人的商标,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将难以描述;第二,商标的使用必须限制在适度与必须的范围内;第三, 使用者不能进行任何关于得到商标持有人赞助或支持暗示的行为。”{18}从本质上看,这三项条件分别从使用的必要性、使用的适度性以及使用的非暗示性这三 个方面,为“Nominative Fair Use”规定主观和客观限制。
依照上述条件,上诉法院对本案分析如下:首先,使用的必要性。事实上,人们在不熟悉“街边新仔”的名称时无法谈论这个组合乐队。因 此,“Nominative Fair Use”的第一个条件是符合的。其次,使用的适度性。报纸广告对“新街边仔”商标的使用是在说明民意测验内容的必要程度内,并且没有在此范围外使用的区别 性标志或者“新街边仔”的任何其他信息。因此,“Nominative Fair Use”的第二个条件也符合。最后,使用的非暗示性。本案中,两份报纸广告没有进行任何获得“新街边仔”赞助或支持的暗示。The USA Today甚至还向读者提出了“the New Kids”是否会走下坡路的问题,这恰恰表明了与赞助或支持相反的关系。显然,“Nominative Fair Use”的第三个条件也是满足的。
应当指出,“Nominative Fair Use”的提出,不但解决了为了说明自己与他人的经营项目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情况下对他人商标的合理使用问题,同时为该种合理使用的成立设定了与 “Classic Fair Use”不同的要件。这样,通过“街边新仔”案的审理,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创设了与“Classic Fair Use”并行的“Nominative Fair Use”理论,提出了判定“Nominative Fair Use”抗辩的三要件,从而标志了商标合理使用理论在整体上的形成。由此,“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一起,构成了商标合理使用理论的基本框架。
(二)“海滩男孩”案:对两类合理使用的区分
商标合理使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以后,在实践中却遇到了难以区别适用问题。例如,在2002年的“花花公子”案中{19},加利福利亚地区法院认为被 告对原告商标的使用既属于“Classic Fair Use”又属于“Nominative Fair Use”。这种将两种形式商标合理使用不加区分地适用的做法,在理论上淡化了两类合理使用的区分意义,实践上混淆了两类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直到2003 年“海滩男孩”案{20}一案中确立的。的判决,才从根本上分清了两类合理使用的适用对象。
此案中,“海滩男孩”(Beach Boys)是一个乐队的名称,该乐队是1961年由包括A1 Jardine与Mike Love在内的五人创建。乐队成立后,创作了很多畅销歌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在全美拥有众多听众。1967年,“Beach Boys”成员组建了“Brothers Records, Inc.”(简称 BRI)以持有和管理“Beach Boys”名下的知识产权。数年之后,Jardine 与Love不再参加共同巡演,并分别组建了自己的乐队。Love乐队获得BRI授权使用“The Beach Boys”商标。Jardine也试图获得该项授权,但因其条件不符合BRI的要求而被拒绝。此后,Jardine的乐队继续使用包含“Beach Boys”商标的乐队名称进行演出。由于两个乐队都以“The Beach Boys”或近似的名义巡演,演出组织者在预订了Jardine的乐队后,有时弄不清到底是哪支乐队会来。很多观看过Jardine表演的人也抱怨,他们 搞不清到底是谁在表演。1999年4月9日,BRI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主张Jardine侵犯
其商标权。地区法院最终作出了支持原告的初审判决,Jardine对此判决不服,于2002年12月上诉于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在上诉审中,Jardine坚持认为他对BRI商标的使用既属于“Classic Fair Use”又属于“Nominative Fair Use”,并根据上诉法院在“New Kids”案中提出的区分两类合理能够得标准提出:第一,他使用“The Beach Boys”商标来描述“Beach Boys”的产品,因此应当适用“Nominative Fair Use”分析;第二,作为另一选择,他使用“The Beach Boys”商标只描述他自己—— Beach Boys的创始成员——根本没有描述Beach Boys的产品,据此又应当适用“Classic Fair Use”分析。
针对Jardine的抛出的难题,上诉法院另辟蹊径,从商标的两层含义的角度指出:Jardine没有使用“The Beach Boys”商标来表示它第一层的描述性含义,即“常去海边沙滩的男孩”。反而,Jardine是在第二层含义,即商标的意义上,使用“The Beach Boys”商标,也就是在表示这个乐队——它的成员——流行的加尼福利亚冲浪文化(popularized California surfing culture)。事实上,无论Jardine使用该商标指向他自己,还是他的乐队,就是因为Jardine没有在该标志的第一层描述性意义上使用,所以 不能适用“Classic Fair Use”。
这样,本案只能在“Nominative Fair Use”的范围内进行。最后,上诉法院对照在“街边新仔”一案确定的“Nominative Fair Use”抗辩的三个条件,认为Jardine对“The Beach Boys”商标的使用,暗示受到了商标持有人的赞助或者支持,没能满足“Nominative Fair Use”的“非暗示性使用”要件,最后判定Jardine败诉。
本案的判决在商标合理使用理论发展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两类合理使用的适用判定的判定上。在“街边新仔”案中,法院将“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进行区别的依据是“使用目的”的不同,前者是为了描述使用者自己的商品,而后者是为了指向商标权利人的商品。然而,这种“使用目的标准”在使用者 本身与商标权利人或其商标或服务有事实上的关联的时候,如本案中的Jardine与“Beach Boys”乐队,由于使用者对商标的使用兼有两种目的,因此也就无法再对两类合理使用进行区分。本案中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使用目的标准”无法区 分两类合理使用的情况下,突破原有的理论,向前跨出了具有的重要意义的一步,提出了“使用信息标准”,从而彻底解决了“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的适用问题,这是对合理使用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另外本案的判决对“Nominative Fair Use”构成要件的运用也有实际意义。“街边新仔”案的判决给出了“Nominative Fair Use”的三要件,即必要性、适度性与非暗示性。应当指出,这三个要件的提出是以“Nominative Fair Use”为对象的,因此也都是从使用行为本身而言的,即使用的必要性、使用的适度性与使用的非暗示性。有人认为,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本案中将被 告使用行为的“非暗示性”要件转化为消费者感觉的“非混淆性”要件。对此,下文将给予深入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认识。
四、商标合理使用的本质与运行机理
知识产权的价值在于使用而非占有,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也就是对知识产权利用的保护。从整体上来看,对商标的使用是对商标荷载的信息的使用,而由于商标的信息构成较为复杂,对商标中不同层次信息的利用其性质与后果也是不同的。
(一)“第一含义合理使用”与“第二含义合理使用”
总的说来,任何一件商标标志都包含两个层次的信息:第一,商标标志本身所具有的一般意义信息,如苹果标志之于一种水果;第二,商标标志本身与特定商品 关联所荷载的特定商品信息,如苹果标志之于一种手机。在商标法领域,前者被称为商标标志的第一含义,后者即为商标标志的第二含义。可以认为,一个标志或符 号只有当其与特定的商品进行关联,荷载了该特定商品的信息以后才能成为商标;只有第一含义的标志不能成为商标,而只对第一含义信息的利用也就不构成对商标 的使用。正是有基于此,美国的《兰哈姆法》才对其第33条(b)(4)所规定的抗辩事由称为非商标性使用(otherwise than as a mark)。
在“街边新仔”案中,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发现被告使用“街边新仔”商标之目的是用来指向“街边新仔”本身而不是被告自己的商品,认为本案被告对 原告商标的使用不属于“Classic Fair Use”,从而确认了“Nominative Fair Use”抗辩。然而,由于这种“使用目的标准”没有在本质上反映商标合理使用的运行机理,这也为后来在两类合理使用抗辩的适用问题上埋下隐患。直到 Jardine在“海滩男孩”一案中的发难,才“逼使”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不得不彻底放弃其所建立的“使用目的标准”,而另辟“使用信息标准” {21},这样才从根本上解决了两类合理使用抗辩的适用问题。
从本质上看,商标合理使用的运行机理在于对商标标志所荷载的不同层次信息的利用:“Classic Fair Use”是对商标标志第一含义的使用,而“Nominative Fair Use”则是在第二含义的意义上对商标标志的使用。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对“Classic Fair Use”与“Nominative Fair Use”这对商标合理使用术语的翻译一般有三个角度:第一,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如将“Classic Fair Use”译为“传统合理使用”,将“Nominative Fair Use”译为“被提及合理使用”;第二,按照法律依据翻译,如将“Classic Fair Use”译为“法定合理使用”;第三,按照“使用目的标准”翻译,如将“Classic Fair Use”译为“描述性合理使用”,将“Nominative Fair Use”译为“指示性合理使用”或“指明商标权人的合理使用”。这些译法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翻译对象的内涵,都可谓译之有据。只是,基于对商标合理使用运 行机理的认知,本文认为对这两类商标合理使用的术语,应当以“使用信息标准”为依据,分别翻译为“第一含义合理使用(Fair Use of First Meaning, FUFM)”和“第二含义合理使用(Fair Use of Secend Meaning, FUSM)”,如此不但能说明这两类合理使用的本质,同时也从内涵上阐明了这两类合理使用的区别。
(二)混淆的可能性与两类合理使用的成立
非混淆性,是商标存在的基本价值,也是商标保护的基本目标。毋庸置疑,对非混淆性的态度,也是正确理解与掌握商标合理使用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
1.第一含义合理使用与混淆的可能性。前文论及,第一含义合理使用在本质上并非是对他人商标的使用,而是对他人商标标志中含有的公有领域内的描述性信 息的利用。由于这些公有领域内的信息,并不能因为被作为特定商标标志而完全私有化,其公有性不会因此而失去;所以他人在公有信息领域内,即在第一含义层面 上对商标标志的利用,当不受商标权人的控制。这也是第一含义合理使用存在的法理基础。就商标权人言之,他通过赋予公有领域内的信息第二含义,从而完成一个 完整的商标“制造”过程。然而,公有领域内的信息——商标标志的第一含义,不但不会因为商标权的存在而被私有;相反,私有领域内的信息—商标标志的第二含 义,则应为其对公有领域内信息的利用而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就是商标标志的第二含义,因其对商标标志的第一含义的关联,而应当忍受他人在利用公有 领域内第一含义信息时,有可能造成的与第二含义的混淆。正是基于上述认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持久美容”案中认为:消费者混淆的一些可能性与合理使用是 可以并存的。当然,这里的并存也并非没有限度,合理使用对混淆的可能性的容忍不能突破第一含义合理使用的第二个要件,即“正当和善意”的范围。换言之,混 淆的可能性对第一含义合理使用抗辩是否成立的作用不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通过正当与善意要件来实现。
由于对此问题的认识没有到位,我国一些法院在审理第一含义合理使用相关案件时,没能把握问题的核心。例如,在“联友卤制品厂诉柏代娣”一案中 {22},被告对原告商标的使用显然不能适用第二含义合理使用分析,而应采用第一含义合理使用分析。尽管本案的一审与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相反,但均将作为 事实问题的“混淆与误认”当成判决的依据,而不是以作为法律问题的“正当与善意”作为分析的核心,以致一审法院因“被告柏代娣在同类商品上突出使用‘茅 山’字样”而判定其侵权;二审法院又是首先认定“‘茅山’二字是因地而知名,不是因商标而知名”等问题。事实上,对于第一含义合理使用的抗辩,无论使用者 如何“突出”使用包含在他人商标中词语,也无论该词语是否“知名”都不妨碍其抗辩的成立。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在该词语的第一含义上,正当、善意地使用。
2.第二含义合理使用与混淆的可能性。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的包括非暗示性在内的,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这三个要件,是从使用行为本身的性质来 要求,而非从一般消费者感觉的角度来判断的。当原告通过证明混淆可能的存在,而支持其侵权指控时,由于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设立,使得被告不必再承担证明非 混淆可能的责任,就可对原告的侵权指控进行抗辩。{23}然而,该理论随着1992年“街边新仔”案的判决而确立以后,却遭致了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有学 者就认为:“用第二含义合理使用抗辩取代混淆可能性分析,这貌似有益的做法却严重背离了商标法的原则”。{2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产生了混淆的可 能,那么有可能是被告的暗示,还有可能是比暗示更严重的明示。就此而言,非暗示性要求比混淆的可能要求更加严格。这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街边新 仔”一案中确立的第二含义合理使用,是在商标侵权指控中为被告提供的一项免责事由,而不是对被告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也就没有第二含义合理使用存在的必 要。
到了2003年的“海滩男孩”一案,法院不再强调非暗示性本身的分析,而是证明Jardine行为在消费者中造成的混淆,来证明Jardine对 BRI商标大使用没有满足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三个条件。这实际上也就给人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第三个条件由原来的非暗示性,变成了非混 淆性。问题是,如果被告能够证明自己对原告商标的使用并没有在消费者中造成混淆,那还用得着所谓的合理使用抗辩吗?况且,“在街边新仔一案中为了帮助被告 而确认的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唯一不同是,比Sleek-craft增加了更繁杂的证明责任。换言之,对被告来说 Sleekcraft test比Jardine版的第二含义合理使用更加容易达到。”{25}有基于此,有学者断言:“为了和商标法取得一致的对此原则的拯救的实际效果,第九 巡回法院通过采用额外的检测无形中放弃了第二含义合理使用。”{26}
本文认为,如果说第一含义合理使用是在公共大道上行走,那么第二含义合理使用则已进入私有土地了。因此,第二含义合理使用抗辩成立的前提就是“使用的 必要性”,也即非此而无其他办法,就如同相邻权中只有经过他人土地,否则无法出入一样。虽然,基于“使用的必要性”,法律允许他人对商标第二含义信息进行 有限的使用;但是,由于是对他人纯粹私人权利的利用,那么这种利用就不可能不影响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在深入分析这种使用的性质之前,考察一下物权法对相 邻权性质的认定至为重要。
物权法关于相邻权的界定,通说为:“相邻权亦称相邻关系,谓相邻接不动产之所有人间,一方所有人之自由支配力与他方所有人之自由排他力相互冲突时,为 调和其冲突,以谋共同之利益,以法律规定直接所人权利之总称。故相邻权为所有权之限制或扩大。”{27}“所谓相邻关系是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所有人 或占有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时,相互之间应当给予便利或者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28}“相邻关系依存于相邻不动产的 所有权关系或使用关系,其实质是相邻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扩张或限制。”{29}上述关于相邻权或相邻关系性质的表述虽然不尽一致,但都认为相邻权或相 邻关系,在本质上是相邻不动产各方权利人的相关权利的限制与扩张关系。之所以产生这种限制与扩张关系,“盖不动产既系位置固定不移之物,而天下之不动产又 不能尽归一人所独有,则甲之不动产与乙之不动产,势必结邻,加以居今之世,又非古人所谓‘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因而相邻间彼此权 利之行使,即难免发生冲突,此种冲突若不解决,则直接影响于所有物之完全利用者固大,间接影响于社会秩序及国民经济者亦复不小,为此法律对于各所有权之内 容,即不能不于一定之范围内加以限制,同时对于各所有权人亦不能不于一定之范围内,课以协力之义务,必能调和双方之利害,而期达到共存共荣之目的。此种所 有权有时受限制,有时得扩张之情形,即所谓相邻关系是也。”{30}“调和利害,共存共荣”,这是相邻权产生的法理基础,也是商标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正当 性依据。可见,相邻权所限制与扩张的对象,是物的利用关系,即物权法的物尽其用宗旨使然;而非物的归属关系,非物权法定份止争要求的结果。对此,日本民法 学家我妻荣先生就有精辟论述:“相邻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对‘利用’的调节,而非对‘所有’的调节。”{31}
正如相邻权的产生的客观前提是不同权利人不动产的事实邻接一样,非利用他人的不动产权利无法发挥自己不动产的效用;商标第二含义合理使用产生的客观前 提则是不同商品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的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的产品或服务与被使用商标存在事实上的关联,非使用他人商标无法准确地说明自己的商品或服务,消费 者也无从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它们在本质上都不是权利归属的重新分配,而是对权利使用的协调。对商标使用者来说,是其权利的扩张,对商标权利人来 说是其权利的限制。既然是对商标权利的限制,那么就不再依据混淆的可能标准来作为这种合理使用成立的依据,否则就是商标权的一般保护,而第二含义合理使用 意义下对商标权利的限制也就无从谈起。本文认为,这正是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街边新仔”案中,将第二含义合理使用的第三个要件设定为“非暗示”, 而不是“非混淆”的根本原因。
另外,也有必要对暗示与混淆的关系作一常分析。暗示,作为“混淆的可能性这枚硬币的一面”{32},虽然有可能导致消费者混淆或误认的后果。但是,从 性质上看,二者本质并不相同,前者是基于商标使用行为本身合理性的考量,后者则是基于消费者的认识状况的考量;从因果关系上看,二者亦无必然关联:首先, 暗示并不一定导致混淆,“你这厢暗送秋波,他那里不解风情”的情况,显然也是有的;其次,混淆也并非一定因暗示,因为混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明示会直接导 致混淆。换言之,暗示并不必然致混淆,混淆也并非一定因暗示。暗示要件的提出,完全出自使用行为本身的性质,即使用行为合理性的考量。
(责任编辑 罗刚) 【注释】
{1}Biyan A. Garner Editor in Chief, Black's Law Dictionary(Eighth Edition),2004West, a Thomson business. P.634.
{2}Bryan A. Garner Editor in Chief, Black's Law Dictionary(Eighth Edition),2004West, a Thomson business. P.634.
{3}武敏:《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初探》,载《中华商标》,2002年第7期;傅钢:《商标的合理使用及其判断标准——从〈商标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谈起》,载《电子知识产权》,2002年第12期。
{4}王迁著:《知识产权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1页。
{5}袁杏桃:《试论商标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建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4期。
{6}例如,在作品中为叙述某一情节,而使用商标。
{7}The “fair use” defense codified in section 33(b)(4) of the Lanham Act, 15 U. S. C.§1115(b)(4).
{8}如邱进前:《美国商标合理使用原则的新发展:TheBeach Boys—案评析》,载《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5期;冯晓青:《商标权的限制研究》,载《学海》2006年第4期。
{9}BLI Editorial Staff, Corporate Counsel's Guide to Trademark Law, Thomson/West, 2006. p4.071.
{10}陈樱琴、叶玟妤著:《智慧财产权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63页。
{11}Robert P. merges Peter S. Menell Mark A. Lemley Thomas M. Jor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Publishers 2007, p.712
{12}KP PERMANENT MAKE-UP, INC. v. LASTING IMPRESSION I,INC.,et al.,543 U. S.03-409(2004).
{13}“the Lanham Act”,60 Stat.427,as amended, 15 U. S. C.§1051 et seq.,规定商品或服务标志的使用者有机会向PT0寻求注册,15 U. S. C.§1051,1053.如果一项注册满足不间断连续使用5年的进一步条件,“商业使用该注册商标以表明商品来源)的权利”将在此外获得“无可置疑”注 册。
{14}328 F.3d 1061(2003).
{15}The establishment of a legally required rebuttable presumption.
{16}如杜颖:《指明商标权人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一以美国法为中心的比较分析》,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9期;武敏:《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初探》,载《中华商标》2002年第7期。
{17}New kids On The Block v. New America Publishing, Inc.971 F 2d 302(9th Cir.1992)
{18}971 F.2d 302(9th Cir.1992), P 308.
{19}Playboy Enterprises Inc. v. Terns Welles.279 F.3d 796(9th Cir.2002)
{20}Brothers Records, Inc. v. Jardine.318 F.3d 900(9th Cir.2003)
{21}这里“使用目的标准”与“使用信息标准”的提法,是本文作者根据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区分两类合理使用的不同依据所总结提出的,而非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直接提法。
{2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8期,第37页。
{23}Brothers Records, Inc. v. Jardine.318 F.3d 900(9th Cir.2003)
{24}Chad J. Doellinger, Nominative Fair Use: Jardine and the Demise of a Doctrine,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ume 1,Issue 1(Spring 2003).
{25}Chad J. Doellinger, Nominative Fair Use: Jardine and the Demise of a Doctrine,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ume 1,Issue 1(Spring 2003).
{26}Chad J. Doellinger, Nominative Fair Use : Jardine and the Demise of a Doctrine,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ume 1,Issue 1(Spring 2003).
{27}史尚宽著:《物权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本文笔者所加。
{28}法学研究编辑部:《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本文笔者所加。
{29}彭万林主编:《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本文笔者所加。
{30}郑玉波著:《民法物权》,北京:三联书局1986年版,第77页。
{31}[日]我妻荣著:《物权法(民法讲义II)》,东京:岩波书店昭和27年刊行,第185页。
{32}Jardine, 318 F.3d at 908 n.5(9th Cir.2003).
网站创始人
- 个人简介:(学术)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
- 邮箱:fengxiaoqingipr@sina.com
-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
- 个人简介:(实务)
- 最高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首届研究员
- 中欧仲裁中心仲裁员
- 深圳、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 中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审判研究会知识产权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热点文章排行
联系我们更多>>

- 通讯处:(Zip:100088)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Zip:100088)
点击进入免费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