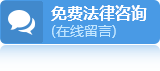试论滑稽模仿对我国著作权法的挑战
来源:知识产权学术与实务研究网 作者: 时间:2006-11-03 阅读数:
●刘淑华*
[内容摘要] 滑稽模仿颠覆了传统著作权制度正当性的基础。认为“滑稽模仿要么侵权,要么属于合理使用”的争论存在逻辑漏洞,滑稽模仿并不侵犯作者的复制权、改编权、汇编权、修改权或保护作品完整权,也区别于“个人使用”或“引用”的合理使用情形。应当围绕“独创性”和“形式”这两个作品的构成要素对滑稽模仿的合法性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 滑稽模仿 合理使用 独创性 形式
2006年初风靡网络的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与影片《无极》之间的侵权争议最终因当事人在法律面前鸣锣收兵已归于平静,但由此带动的网络“恶搞”[①]却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将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律制度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我国《著作权法》并没有对此类作品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缺乏相关纠纷判决的先例,这不能不说是著作权法在网络环境下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正如科殷教授所言,“倘若人们为法的形成寻找一个公式,那么,托因比在为整个文化所创造的一对概念在这里似乎最恰当不过:挑战(Challenge)和回应(Response)。”[②]本文无意对《馒头》事件引发的文化、经济、法律和道德等各个层面的回应作出全面梳理或评价,此为笔者力未能逮,拟仅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对此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滑稽模仿挑战传统著作权制度的正当性
“最为高级的那种滑稽模仿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诙谐的、在美学上令人满意的散文或韵文形式的作品,通常不带有恶意,在其中,通过严格控制的歪曲,一部文学作品一个作者或者一个派别或一个作品类型的主题和风格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被以一种方式来表达,而这种方式能够导致对原作产生—种含蓄的价值判断。”[③]而解构主义哲学认为,滑稽模仿是指后现代作品中对各种经典文本和传统文学作品本身的解构,以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性,或者借用上述表现形式对现代生活进行解构。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滑稽模仿,主要从规范的角度而言,是指具有这种后现代创作风格的滑稽模仿作品,而创作风格或创作方式本身并不能成为著作权的保护对象。
滑稽模仿自古有之,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时期,“parody”一词就被用来表示对史诗的滑稽(comic)模仿及改造(transformation),它既包含了滑稽的一面又包含了互文的一面。但自文艺复兴始到19世纪,受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它被视为一种低劣的文学形式。在20世纪的50年代以前的现代主义时期,它又跃居为一种“形式革命”,而大加赞扬的是其互文性的一面。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它又不仅保留了互文性的一面,而且还恢复了滑稽的一面。至此,滑稽模仿这一双重编码“既编进了现代的又编进了古代的含义。”[④]后现代主义的滑稽模仿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滑稽性。后现代的滑稽模仿超越了低劣的滑稽性,不再是由主体的错误或者丑怪所引起的,相反,创作者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平等态度,通过在模仿原作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或颠覆其内容,造成仿作和原作似曾相识却产生截然不同的滑稽和幽默效果。
2.互文性。滑稽模仿通过借用原作的某些特征以唤起或建立(conjure up)二者的“互文”关系,达到对原作的记忆、重复、对比和修正,使作者和读者在感受两种文本差异的急速心理落差中领会滑稽模仿的戏谑和狂欢。
3.通俗性。滑稽模仿的对象是已经为大众所耳熟能详的传统或经典文学作品,也可以曾经引起轰动的电影和畅销书。滑稽模仿将这些经典文本拿下神坛进行通俗化创作,使人们不再囿于对伟大艺术家和经典作品的顶礼膜拜,从而消解平民写作与精英创作之间的界限。
4.形式性。滑稽模仿往往依托多个经典文本,拼贴众多文献资源,以夸张和超乎常理的叙事方式来表现一种简单的意义或浅显主题,其场面化、形式化的表现压倒了内涵的深掘,使滑稽模仿的狂欢大于思索,娱乐多过审美。滑稽模仿在形式上还可能打破情节的连贯,在各个片断中插入了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广告语、名人名言、流行歌曲、人物名字、商标名称等,它们零乱的堆积构成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拼贴画”(collage)。
5.“无厘头”意识。“无厘头(Without Culture)是指故意将一些毫无联系的事物现象等进行莫名其妙地组合串联或歪曲,以达到搞笑或讽刺目的的方式。”[⑤]滑稽模仿的颠覆与批判姿态,深得后现代文化的浸润,但它并非纯形式的舞蹈,而是通过对原文看似不经意的裁剪拼接后,形成“有意味的形式”。
著作权法作为调整和规范文化艺术领域的知识创造活动的基本法律,一定时期的文艺思潮和文化渊源会深刻影响著作权法正当性的理论基础以及制度选择。由于文艺思潮的更替,集中体现后现代文化精髓的滑稽模仿与传统著作权制度的冲突成为必然。
从传统著作权法的文化渊源来看,18、19世纪的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对著作权正当性产生深远影响。浪漫主义风格强调主观、主体性和创作个性,注重情感表现,认为作品是作者的人格再现或外化,这种著作权“人格权”理论一直盛行至19世纪末,由此奠定了作者权体系关于人格权和财产权二元著作权观念正当性的理论基础。自20世纪以来,文艺思潮整体上沿着“从主体本位到文本本位”的路径不断发展。在20世纪的前50年,表现美学仍然雄踞了整个现代主义文艺时期,滑稽模仿在现代派作家那里被当作是一种“形式革命”,带有“崇高的”美学目的,即用作标新立异的表现形式,让人看到的是个人主义、个人风格或精英文化,并且这种独特的形式最终是为作品的终极意义服务的。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时期以来,主体观和表现论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几近消失了。滑稽模仿这种艺术形式被用作主体消亡的见证,让人看到的是作品的虚构性。在滑稽模仿作品中没有所谓终极意义、深度和本质,一切都是文本和互文本,借助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不和谐,形式和内容的相矛盾,语言和语境的不一致,用一种玩笑方式消解它所叙述对象的整体性、同一性和普遍性,在被模仿的原文中,读者看到的是互文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游戏性”。正如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东西,不存在言外之意,没有决定作品终极意义的绝对真理”。[⑥]如此,“就个人而言,主体消失了。就形式而言,真正的个人‘风格’也就越来越难得一见了。”[⑦]
滑稽模仿独特的后现代文化品格颠覆了传统著作权法中作者对作品的统治地位。作品中主体本位的消解意味着“作品是作者人格表现”的传统著作权理念以及“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理等将面临重大挑战。根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文学艺术领域的社会实践是第一性的,是著作权法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必将引起规范文艺创造活动的著作权法正当性理念和具体制度的嬗变。
二、关于滑稽模仿合法性的理论争论及制度回应
尽管中国尚欠缺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土壤,但通过各种传播途径受到普遍欢迎的滑稽模仿已经彰显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引起人们对这种行为合法性的关注。关于滑稽模仿的法律性质在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存在不同的制度实践。
(一)理论争论:自由使用还是非自由使用?[⑧]
不少学者从著作权法鼓励创造的宗旨出发,认为应当对滑稽模仿体现的独创性劳动进行保护,滑稽模仿对原作的借用属于合理引用。也有学者从保护公民言论和表达自由出发,主张对滑稽模仿这种特殊的文艺批评和评论方式持宽容态度,法律应当规定滑稽模仿对其他作品的使用属于自由使用。
另有一类观点认为,滑稽模仿作品“是一种在内容安排和表现形式上富有独创性的演绎作品”,[⑨]未经授权的滑稽模仿侵犯著作权人的改编权;由于滑稽模仿作品复制、传播、汇编了原作受著作权保护的片断,还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汇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就著作人格权而言,滑稽模仿擅自改动作品,歪曲、篡改了原作的思想观点,也涉及侵犯著作权人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二)两大法系的不同制度实践
在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例如瑞士、西班牙、巴西、法国、贝宁、布隆迪、喀麦隆、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等,都在立法中明确将滑稽模仿规定为对著作权的限制。《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则要求成员国在本国立法中引入滑稽模仿作品的豁免制度。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著作权及有关权利之制度》也规定滑稽模仿属原创作品。但德国和荷兰的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授予滑稽模仿作品的特别豁免,而是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情进行裁判。例如,德国联邦法院认为,人们不能不加区别地一律认定其为自由使用行为,它们有时候也会构成对作品的演绎或者其他形式的改编。[⑩]
与英美法的经验主义传统相适用,普通法系国家并没有对滑稽模仿进行立法规范,而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案例建立起有关滑稽模仿的法律原则。尽管理论上也有观点认为滑稽模仿属于演绎作品,应当受到原作著作权人的控制,[11]然而法院在裁决有关滑稽模仿的许多版权纠纷中,都倾向于运用合理使用原则为其提供保护。但相似的案情在不同的法官裁量下却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在Original Appalachian Artworks, Inc. v. Topps Chewing Gum, Inc.案中,美国联邦法院拒绝给予一种纯喜剧性的滑稽模仿以合理使用的保护;[12]在Leibovitz v. Paramount Pictures Corp.案中,上诉法院认为由于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具有合理使用的合法目的,认定被告的滑稽模仿行为构成合理使用;[13]而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一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即使以商业目的利用他人的著作仍然可以主张合理使用。[14]
(三)对现有理论和制度的评析
1.对现有研究思路的逻辑分析
大体上来说,现有的理论争议不外乎围绕以下思路展开:滑稽模仿要么侵权,要么构成合理使用。如果滑稽模仿构成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显然就不构成侵权,反之则反。乍一看,得出滑稽模仿侵权或者不侵权的结论似乎不存在逻辑上的遗漏,因为此种思维模式作为一个形式逻辑上的选言判断,穷尽了关于滑稽模仿侵权与不侵权的两种现实可能性。然而,“滑稽模仿要么侵权,要么构成合理使用”这一选言判断并没有穷尽所有的选言肢,合理使用只是不侵权的一种情形,还存在其他侵权例外和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情形,以及并没有落入著作权专有范围而属于完全自由使用的情形,后者典型的如对公有领域的素材或者对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成分进行滑稽模仿就不能被认为侵犯著作权。因此,“滑稽模仿要么侵权,要么构成合理使用”这一思维模式存在逻辑漏洞,以此作为论证前提必将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
2.与滑稽模仿有关的侵权概念之辨析
主张滑稽模仿属于非自由使用的理论实质上提出了滑稽模仿与复制、演绎、汇编的分界线以及滑稽模仿与精神权利(主要涉及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冲突问题,对该理论的评价必须从厘清滑稽模仿与相关著作权概念入手。
(1)滑稽模仿与复制、演绎、汇编的界分
滑稽模仿“侵权说”基于以下认识:由于著作权不仅存在于作品的整体当中,也存在于组成整体的片断之中,这些片断可以视为一个个独立的小作品。例如,《馒头》复制了《无极》的大量片断并加以改编,连同央视的节目片断和一些音乐片断等将这些小作品汇编成《馒头》,并在网络上进行传播,因此《馒头》侵犯了《无极》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改编权、汇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15]笔者认为,对这一观点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判断作品或作品片断是否受保护的前提在于是否具有独创性,如果笼统地认为著作权法保护所有作品或者构成作品的所有片断,则会陷于一种著作权扩张的绝对理念,妨碍再创作的自由,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
第二,即便按照上述观点,《馒头》改编了《无极》片断并加以传播,也并没有侵犯原作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因为复制的含义是指没有增加再创造成分的对作品的“再现”;作品的网络传播也只是改变了作品的载体而没有增加新的创作内容。只要滑稽模仿增加了新的独创性的成分,就不能视为侵犯原作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第三,同样都是以原作为基础进行的再创作,滑稽模仿与改编对原作的依赖程度也不同,其独创性程度存在差别,二者具有不同的特点。改编是原作和派生创作双重创作活动的产物,既保留了原作的独创性又体现了改编行为本身的独创性。如果完全脱离原作的独创性进行的重新创作属于重编,构成一部独立的原创作品,而不是属于改编作品;如果对原作进行不具独创性的删除、简略或者校对,也不构成改编作品。同时,改编把材料在新的语境中仍然强调内在意义结构上的一致性,而滑稽模仿则把所借用的材料在新的语境中完全改变、夸张或者扭曲其本来的意味,强调符号意义的间离而非统一。因此,不能笼统地将滑稽模仿视为或不视为对原作的改编,而应当根据滑稽模仿的独创性程度进行具体分析。
第四,任何作品都可以分解为各个片断,如果将各个作品的片断视为一个个小的作品,必然导致对任何作品都视为汇编作品,这显然抹杀了不同的作品类型。从哲学角度而言,这是将作品形式的部分与整体混为一谈,犯了以部分取代整体的认识错误。
(2)滑稽模仿与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区别
修改权是指作者自己修改或授权他人对作品形式进行修改的权利,它既包括由于作品内容的变化而导致的对作品形式的改变,也包括在作品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对作品纯形式的改变。修改权是对原有作品形式的修改完善而并非产生一部新的作品,这是判断滑稽模仿是否侵犯修改权的关键。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修改权的进一步延伸,它从反面规定禁止对作品的内容进行歪曲、篡改。因为“歪曲、篡改作品的思想情感必然破坏作品的原有形式,损害原作品形式上的完整性。所以,著作权法通过保护作品形式上的完整,就可以避免作品被歪曲和篡改。”[16]因此,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本来含义在于保护现有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并不能约束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行为。一言以蔽之,只有滑稽模仿产生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新作品就不能视为侵犯原作著作权人的修改权。在实践中,被指控侵犯作者的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主体也大多数是图书出版者及报社、期刊社。
3.滑稽模仿与合理使用相关情形的区别
(1)滑稽模仿不同于个人使用
首先,从使用的目的来看,法律明确规定个人使用限于学习、研究或欣赏等非营利性目的,然而正如美国联邦法院所主张,即使滑稽模仿以商业营利为目的仍然可能构成合理使用。[17]
其次,从使用的主体来看,个人使用只限于满足个人实现上述目的,而不能扩展到第三人或单位。但滑稽模仿的使用主体并不限于个人,并且作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得到广泛传播,如果加以使用主体限制,就会不合理地阻碍文学艺术的进步,有损社会公共利益。
再次,从使用方式上来看,个人使用的方式主要限于复制,也可以包括对作品进行改造(翻译、改写、音乐改编等)。如上文分析,如果滑稽模仿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体现了较高的独创性,显然并非对原作的简单复制,也并非对原作的改编。
(2)滑稽模仿也不同于引用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引用除了要求必须是作者授权公开发表的作品外,引用的内容必须忠实于原文,引用的方式主要限于介绍、评论或说明,并且“只能为了教学研究目的进行引用,不得超过为引文确定的正当范围”。[18]而滑稽模仿并非忠实于原文,相反它是对符号原有意义的背离,也不限于非营利性的教学研究目的。滑稽模仿的对象一般是众所周知的经典作品或有广泛影响的作品,无需在仿作中加以介绍或说明。况且,滑稽模仿也不能视为通常意义上的文艺批评或评论,这是因为:
首先,滑稽模仿虽然也深得后现代文化的批判个性,但批评和评论不是滑稽模仿作品的主要目的,娱乐性和喜剧性才是滑稽模仿的禀赋和主旨。很难想象一部缺乏幽默和戏谑精髓的批判性作品仍然可以称得上滑稽模仿作品。
其次,即使对于批评性的滑稽模仿,它与一般的文艺批评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受到夸张化、形式化和“无厘头”意识等表现手法和创作风格的限制,而后者更倾向于遵循严格的客观标准,一般依据“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从作品的社会评价和艺术评价两个方面进行科学考察,以达到某种弘扬或改进的目的。
再次,将滑稽模仿视为一种批评或评论,本身还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保护障碍。法院将不可避免地对滑稽模仿所表达的内容即滑稽模仿是否是对原作或相关的社会现象进行评论或嘲讽进行审查,以考虑滑稽模仿所要表达的内容是否与原作有关联以及其关联程度。而作品的内容具有抽象性,不同人具有不同的认识。“由仅仅受过法律训练人来判断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很危险的”,[19]法官并不具备对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审查的能力,也不应当对艺术观点本身做出评价。因此,由法官来充当这种“言论审查官”的角色将十分不利于保护滑稽模仿作品。
三、滑稽模仿合法性的具体分析
目前,有一种代表性观点以作品目的或功能作为判断滑稽模仿合法性标准,认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滑稽模仿特指一种对原作本身进行模仿讽刺或批评的文艺创作形式。[20]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该观点至少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如前所言,忽视了滑稽模仿与“批评评论”的区别,并且以作品的目的或功能作为评价标准必将陷入不确定性的泥淖,造成司法实践的困难。第二,将滑稽模仿的类型局限于批评性滑稽模仿,排除了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以批评为目的或主要目的的娱乐性滑稽模仿,而后者更加符合滑稽模仿的特征,似乎更应当被视为滑稽模仿。第三,即使对于批评性滑稽模仿,该观点只看到了滑稽模仿以原作为“靶子”的情形,遗漏了以原作为“武器”来批评讽刺其他作者、作品或社会现象等的滑稽模仿。
笔者以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指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形式,“独创性”和“形式”是作品的两个构成要素,滑稽模仿合法性的判断也应当围绕这两个要素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应当依独创性标准“过滤”所借用的原作或原作的成分是处于公有领域还是专有领域;其次,对于专有领域的作品进行滑稽模仿,也应当依据滑稽模仿进行“转化”(transformative)的独创性程度进行衡量,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新作的转化成分愈高,就愈不需要考量(美国版权法)第107条不利主张合理使用的各种因素,包括商业目的。”[21]
(一)对公有领域的作品或作品成分进行的滑稽模仿
著作权法上的“公有领域”是人人都可以自由利用的智力资源,既包括曾经被授予财产权但因保护期限届满而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也包括一开始就被法律规定为处于公有领域明确排除受法律保护的作品。如果滑稽模仿所借用的作品来自于公有领域,显然不构成侵权。
按照德国著作权法的一般理论,作品的(表达)形式分为外在形式(aeussere Form)和内在形式(innere Form)。外在形式是指作品可感知的部分,包括文字、线条、色彩、声音等的组合;而内在形式是指在作品的内在结构模式,例如小说的情节、角色、戏剧剧情和绘画的布景等,对于内在形式进行的保护的理由主要在于防止那些“实质性相似”的侵害著作权的行为。但并非所有作品的形式一律受到法律保护,郝普曼(Hubmann)认为,形式可以继续分为具有独创性的形式和不具有独创性的形式。[22]外在形式中一般成分,如文字、体裁、风格、通用符号、节拍等,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而外在形式中的文句构造、韵律组合、色彩调和等具有独创性,就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对于内在形式也应当区分其独创性与否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保护。在实践中,德国联邦法院正是根据上述理论来处理著作权领域的侵权纠纷的。
由此可见,即便对处于专有领域的作品,其保护的成分也仅仅限于其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形式,而并非笼统地保护全部的表达形式。“公有领域”的外延还应当扩大到不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表达形式上。所以,如果滑稽模仿的对象是某一个作者的全部作品的风格,某一种文学类型,或者作品不具独创性的标题、普通事件、平常人物、标准的情节或布局等等,借用一部作品上述处于“公有领域”的成分就不能认为侵权。
(二)对于专有领域的作品或作品成分进行的滑稽模仿
对于专有领域的作品进行滑稽模仿,既存在对先前作品的借用,又注入了或大或小的创造力。滑稽模仿一方面依赖于原作的这些独创性特征,如果没有这些特征就不能达到滑稽模仿这一文学类型的效果,滑稽模仿的含义就会丧失;另一方面,滑稽模仿借用原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向读者介绍或者欣赏原作,而是在必要的限度内唤起或建立仿作和原作之间的“互文”关系,在模仿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或改造。“颠覆是在模仿基础上的颠覆。如在模仿文类或形式的基础上颠覆其内容。……改造指对原文在字、句、形、节奏、韵律、风格、题材等方面的改造。”[23]按照“颠覆或改造”这种转化过程中的独创性大小,可以将滑稽模仿分为:
1.完全转化的滑稽模仿。如果滑稽模仿借用一部或多部作品的某些独创性特征加以剪辑、拼贴或重新编排,那么从整体上来说,仿作体现了完全具有不同于原作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意义结构,构成独立的原创作品。
2.部分转化的滑稽模仿。如果滑稽模仿在外在形式全部“再现”了原作的独创性形式,但对其内在形式进行了转化;或者在内在形式上借用了原作的独创性,但对其外在形式进行了转化,此种滑稽模仿属于广义上的演绎作品。[24]前者如《吉祥馒头》借用歌曲《吉祥三宝》通过改动歌词来讽刺“馒头”事件;FLASH《我不想说我是一只鸡》借用歌曲《我不想说》加以重新填词表达对禽流感这一社会时事的评论。后者如“后舍男孩”翻拍的一系列视频作品滑稽模仿众多歌星MV歌曲中的表演;又如以滑稽的方言或取笑调侃的腔调来演唱严肃歌曲《红太阳》,等等。原则上,部分转化的滑稽模仿无论其目的在于批评讽刺还是在于纯粹的娱乐,也无论其对象是用来当作“靶子”还是“武器”,均应当受到原作著作权人的控制。但考虑到基于滑稽模仿的创作需要,如果所借用的部分是在必要的限度内让人“回应或者想起原作”,并且没有给原作的市场造成替代,同时,取得原作著作权人的授权存在着不合理的交易障碍,那么,此种使用有时也可以被认为是合理使用。
3.没有转化的滑稽模仿。滑稽模仿如果完全复制了原作的独创性形式,无论是在文字、图像、声音、色彩、韵律组合等外在形式,还是情节、主要人物、主题、布局等内在形式上都不加以转化,或者只是进行了不具独创性的简单拼凑或粘贴,此类蹩脚的滑稽模仿实际上是对原作的复制或剽窃,不能适用合理使用原则的保护。
由此可见,“合理使用”的著作权限制只适用于上述“完全转化”和“部分转化”的滑稽模仿。但是,也并非上述两种融入了独创性的滑稽模仿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主张合理使用,能否主张合理使用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当同著作权人就允许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进行交易的费用超过了交易的费用时,使用可说成是‘合理的’”。[25]这种法律经济学的见解在解释滑稽模仿合理使用的正当性上是有力的。就批评性滑稽模仿而言,要得到原作著作权人的许可是非常困难的,著作权人一般不太可能自己进行或许可他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滑稽模仿。然而,一篇滑稽模仿作品并不总是嘲讽或以其他方式批评被模仿作品,或者滑稽模仿可能压根就不是一部批评作品,其惟一的目的可能就是娱乐,那么,对于用作“武器”的滑稽模仿和娱乐性滑稽模仿,为什么也应该得到合理使用的庇护呢?因为著作权人可能担心即使并非批评他,也会对原作受众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减少自己的收入而拒绝滑稽模仿,例如,将作者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当作同性恋或者进行有关色情内容的滑稽模仿时。[26]总之,著作权人可能不愿意以合理的价格许可任何一种滑稽模仿,不管这种滑稽模仿的文学价值有多大,甚至不管它可能并没有对原作市场的产生替代的威胁。现实的交易障碍使滑稽模仿如果需要事先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存在经济上的非效益,因此,应当从法律上允许未经授权的滑稽模仿。
第二,在衡量滑稽模仿作品是否对原作的潜在市场或价值产生替代影响时,应当考虑原作的知名度、仿作的创新性及影响。一般来说,批评性的滑稽模仿并不会对原作的市场造成替代的威胁,他们满足了不同的市场需求。不经作者许可的批评评论本身不啻于对原作的免费广告,而且是特别可信的广告,很少会成为原作的严格替代品,反而可能刺激销售、扩大原作的市场。但是对于娱乐性滑稽模仿,大多数人可能更倾向于喜欢一部作品的诙谐版本而不是严肃版本,特别在”严肃”版本本身纯粹是为了娱乐而并非包含某种道德伦理教育意图或者知识性内容时,滑稽模仿可能对原作的市场或价值形成替代,因而不能一概认为属于合理使用。
第三,就使用的目的和性质来说,使用原作的商业动机并不能当然地否定滑稽模仿的合理使用辩护。 “倘若真要把为商业目的的利用都排除在合理使用之外,那几乎就等于排除了以(美国版权法)第107条其他各款因素主张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因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中,不管是新闻报道、评论、批评、教学等,都或多或少跟利益脱不了关系。”[27]因此,滑稽模仿是否被用来做营利性的使用与其能否获得法律的保护无关,与其可得的保护程度也无关。
第四,在判断滑稽模仿所使用原作的数量和质量时,应当考虑滑稽模仿为了让公众“回忆或联想了原作”,在必要的限度内需要相比通常情况下对原作进行更多和更深入的借用。换言之,应当允许滑稽模仿者借用足够多的东西以使自己的作品能被看出是滑稽模仿。但如果滑稽模仿超过必要的限度借用原作太多的有著作权保护的外在或内在形式,以至于使滑稽模仿成为原作的替代品,就会对原作的市场产生威胁。因此,判断滑稽模仿实质性使用的标准不能机械地进行,它不依赖于所借用原作的相对或绝对数量。
四、结论
当“现存的法的制度并未包含某一种合适的规定,首先应当阐发一条规则来解决尚未规范的案件……,通过形成新的规则,进一步发展法”。[28]为了应对滑稽模仿给我国《著作权法》带来的挑战,我们应当形成新的规则将滑稽模仿列入著作权法的调整轨道。为此,建议在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增加一项,将滑稽模仿列入合理使用的范围并规定其适用条件:
“为了创作滑稽模仿作品可以在作品中适度借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滑稽模仿不得损害作者的人格,不应是原作的真正复制品,也不应与原作相混淆并不得有损其信誉。”
笔者认为,这一规定避免了依作品的目的或功能对滑稽模仿进行狭隘化定义的种种弊端,体现了著作权法对滑稽模仿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同时限制了滑稽模仿适用合理使用的条件,即对原作的借用不得超出“回忆或联想起原作”的必要限度、不得对原作的市场或价值产生替代、也不得侵犯作者人格权等“在先权利”,符合著作权法鼓励创造的宗旨。
[②] [德]H·科殷著,林荣远译:《法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③] J. G. Riewald:“Parody as Critisim”,50 Neophilologus 125, 128-129(1966).
[⑤] 《新华新词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4- 345页。
[⑥] 牛宏宝:《现代西方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8页。
[⑦]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0页。
[⑨] [西]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领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版,第85-86页。
[⑩] [德]M﹒雷炳德著,张恩民译:《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13] Leibovitz v.
[14]
[16]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70页。
[17]
[18] [西]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领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版,第126-127页。
[21]
[22] 施文高:《比较著作权法制》,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617页。
[23] 胡全生:《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24] 广义上的演绎作品可以认为是“基于以前的一部作品所作的任何能产生新作品的改造”。参见[西]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领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版,第80页。
[26] 随着人格权观念在两大法系中的融合,法院认为此种情形下援用合理使用的辩护可能有辱作者的人格而往往判决滑稽模仿者侵权。
[27]
[28] [德]H·科殷著,林荣远译:《法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 个人简介:(学术)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
- 邮箱:fengxiaoqingipr@sina.com
-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
- 个人简介:(实务)
- 最高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首届研究员
- 中欧仲裁中心仲裁员
- 深圳、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 中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审判研究会知识产权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 通讯处:(Zip:100088)
点击进入免费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