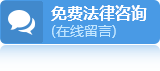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与利益分享
来源:知识产权学术与实务研究网 作者:崔国斌 时间:2009-06-08 阅读数:
科学发现对人类科技进步的贡献,同通常的发明相比,并不逊色。比如在学者经常列举的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焦耳发现电热交换规律等科学发现的例子。这些发现也许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却不能获得专利法的保护。在这一问题上,专利法的逻辑就变成了“某项发现对社会的贡献太大,所以不能授予专利权”。这多少同专利法所坚持的赋予创造者一定特权以促进科技进步的一贯主张相左,因而在一般的公平理念上并不令人信服。这里的问题不在专利法,而在于我们对专利法立法目的错误认识。笼统地说专利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促进知识创新推动社会进步,无异于给专利制度戴上一顶过于宽大和“崇高”的高帽子。其实专利法的立法目的具有很大的功利性,它只对那些能够直接应用于实际产业的实用技术提供保护。至于该技术究竟对人类知识总量有多大的贡献,专利法并不关注,专利法自身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承担其促进整个人类技术进步的重任。它只有在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时,才搬出“促进人类科技创新”之类的目标来。一般认为科学发现的确扩展了人类的知识范围,但并不直接改进现有的产业技能,而发明才增加了人类的实践能力(Practical capabilities),直接与产业紧密相连[33][33]。传统的专利制度不对科学发现所带来的间接利益感兴趣,这就使得“科学发现不授予专利权”这一规则得以确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规则的背后的考虑完全是从产业界的直接的实际利益出发的。从产业界角度看来,专利制度完全是一种商业竞争的工具,产业利益才是根本的法律原则(后文还要具体论述这种趋势的各种影响,这里不再赘述。)。既然,发明同发现的保护与否是利益权衡的结果,那么当某些发现可以直接导致产业应用时,产业界就不惜抛弃或修正上述规则,努力为某些发现的专利保护铺平道路。先前是化学领域对自然物提纯物的专利问题得以解决,现在在生物技术领域同样的问题出现:新的物种、新的基因片段、新的蛋白质分子的发现与分离等,作为科学发现的同时又和实际产业紧密相连。正因为如此,生物产业界越来越早地介入到基础研究中来,希望及早地发现新的产业机会。产业界的介入必然使得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机构迅速私营化,对生物早期基础研究不断上升的研究经费的保护要求自然就越来越强烈,通过专利法尽快获得垄断权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了[34][34]。在专利法领域依旧坚持过去的规则越来越困难,终于,有人直截了当地说,某些情况下,即使是发现也可以获得专利权保护,只要基于此发现的发明(或者干脆说发现本身)是新颍的,富于创造性,有利促进社会技术进步。[35][35]
以上是从专利法立法目的的角度讨论专利法不保护科学发现的深层次原因,接下来我们回顾历史上相同问题在一些国家引发的争论。这种回顾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专利法对发现进行限制的真正原因。
1922年在欧洲的法国,J.Barthelemy 教授向法国 (The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废止关于禁止对科学发现等授予专利权的规定。在该建议中,他提出两点设想:首先,科学家可以获得所谓的原理专利(Patent of Principle),其保护期为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其次,科学家作出某项发现以后,如果他人基于该发现作出某项应用发明,则科学家有权就该发明所获利益主张自己的分额。无独有偶,同一年,意大利的(the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最终批准了Bergson 教授的一项计划草案。在该草案中他说当时专利法对科学发现不给予专利权保护,The Whole Question is dominated by crudest utilitarianism ,empiricism unhappily disguised in scientific nebulosity ,and ,finally ,the most disconcerting arbitrariness .他说J.Barthelemy 教授的建议在法国没有被采纳,是因为法国人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接受该建议以前,如果法国单独对科学发现提供专利保护,则法国的工业将被迫支付比其他国家竞争者要多的许可费用,从而阻碍法国工业的发展。Bergson 教授因此建议,通过创设一项国际条约使各签字国共同来维护科学家的这项权利。这项建议走得相当远——当时(The League of Nations)的专家甚至还着手起草该公约草案。到了1930年,这一努力宣告失败,其结果是政府决定以政府奖励来代替科学专利,给予科学家以奖赏。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的发展,对科学发现进行政府奖励的做法逐渐得到推广。[36][36]学者们解释这一做法是列举了一些理由,比如很难追溯某项应用发明的科学根源、应用发明常常远在科学发现之后不便支付许可费、不利科学界的交流等等[37][37],其实专利制度对任何发明给予保护,都要面临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发明与发现上的表现并不会有质的区别。拒绝对科学发现给予专利保护如果还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的结果的话,那也是经过利益权衡后采取的完全实用主义的做法:不是发现本身固有的属性导致其不适合专利保护,而是发现作为基础研究的一部分社会不愿给予专利保护。在缺乏产业集团的游说的情况下,这一实用主义规则尽管不符合基础研究人员的利益,还是被专利法接受了。
在理论上和立法实践上,我们努力地区分发明和发现,将科学发现明确排除在专利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在司法实践中则应该解释为法院应该象Lord Justice Mustill 在 Genentech v. Wellcome 案中所说的那样——“在审查专利的专利性问题时,必须对该技术方案是否属于发明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即确定技术方案是一种发明以后,法院才能往下走”。 Lord Justice Hobhouse在Biogen v. Medeva 案上诉审中,同样支持这一观点,认为除非该技术方案是一项发明,否则任何权利要求都是无效的[38][38]。可是,在英国享有盛誉的HOFFMANN法官却否定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立法实践中,许多国家的专利法和国际公约中均没有对发明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选择变通的办法--通过约定一系列专利性条件来限定授予专利权的范围,比如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以及一些明确的排除性规定。在立法者看来,不能说不存在不是发明但依然满足上述要件的法案存在,但是至少立法者还没有想到一个例子。司法实践中,法官有时直接依据所谓的直觉就可以说某些对象是发现而不是发明,但是更多的时候,法官不能依据此类直觉,相反,他要求助于所谓的专利性判断[39][39],符合专利性的要求并被一些强行性规定所排除就应该受到专利法的保护。有人会说专利法中都明确将科学发现作为一种排除规定明确宣示,可实际上基因技术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的业已建立起来的法律概念体系,模糊了发明同发现的界限[40][40],甚至说根本就没有界限。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专利法的历史基础是机械和化工技术,而生物技术与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难以为现在的专利法概念所涵盖,[41][41]。这样,专利法对科学发现的排除规定基本对法官起不到什么作用,法官实际上是在依据专利性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对一项技术授予专利权,至于该项技术究竟是发明还是发现倒并不重要。
四、我们的结论:淡化发明与发现的区分,严格专利性审查标准
我们的专利法已经接受了自然物质的提纯物的专利请求,这实际上也使我们的专利法走上了同西方国家专利制度基本相同的发展道路,不可能独自偏离这一方向了。我们肯定了提纯物的专利性,那么与此相近蛋白质分子序列、基因序列等就注定要照此办理了。作为一种政策上的考虑,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机会重新考虑自然物质的是发明还是发现的问题——本来应该在很早以前仔细讨论这一问题并适当坚持我们的意见。但是,如前文所述,我们认为专利法上对发明和发现的区分,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随着利益天平的倾斜,这一规则也会被直接或间接地被抛弃。我们简单地将这一规则视为不可退让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取的,以之来抵制我们不愿看到的专利法保护范围迅速扩大的趋势是不现实的。在现在国内国际的商业竞争的环境下,单纯的理论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真的显得很苍白了。
我们说专利法在处理基因序列之类的专利问题面前,淡化所谓的发明同发现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专利法应该立即将“科学发现不受专利法保护”这一规则清除出去。实际上我们已经基于这一规则将很多技术方案排除出专利法的保护范围。人们逐渐把这些排除规定当作公理而接受,如果突然改变这一规则,我们又要借助新的原则或规则来论证这些先前已经被排除的方案不应受到专利保护的理由,势必引起新的混乱。当然,这里蕴涵的假设是过去专利法对保护对象的界定是已经被现在的社会接受。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专利法只有在面对新的保护客体时,才需要重新利用新的原则来考虑问题,或者说抛开表面的规则来考虑问题——不必过分拘泥于发明同发现的区别,更多地关注其他专利性的审查。基因技术就是这样的新客体,没有必要先确定其是发明还是发现,而应直接对之审查三性,符合要求的自然应当授予专利。毫无疑问,我们忽略对发明还是发现的审查,不是因为我们不担心这种策略会给打破传统的发明人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而是我们认为在这些新的客体面前,发明与发现的区分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真正关注这一区分。抛弃过去的规则,是因为我们不愿在这里纠缠不清。为了尽量减小这种策略的消极影响,我们强调应该严格审查此类技术方案的专利性即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等,尽量避免那些缺乏产业实用性等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被垄断,从而防止专利制度成为社会技术进步的障碍。具体如何审查基因技术专利的专利性,这将在下一章介绍。
第二节 基因专利保护与公共政策
生物专利远在生物工程技术引人注目之前便已经存在:第一项有关生物有机体的专利是十九世纪中叶在芬兰颁发的。美国则与1873年对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颁发一项有关无机病原体酵母专利。另外,生物专利已经得到<<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斯特拉丝堡公约>><<慕尼黑公约>>的认可[42][42]。但是早期的生物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甚微,有关专利问题并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
如前所述,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人类开始利用基因工程手段随心所欲地改变周围的生物世界:下至微生物上至人自身,无一例外。此类技术直接影响到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生命对自身的道德观念,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另外,生物基因技术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威力,又加深了人们对其可能被滥用的担忧。这些关注和担忧,在专利法上就成为基因工程技术获得专利保护的阻力。很多人利用专利法中“违背公共秩序不授予专利权”的原则来反对给予基因技术以专利保护。以下就专利法中公共秩序等条款的合理性以及基因技术自身的道德性问题等展开讨论。
一、 专利法中的道德评价的必要性
专利法中的道德评价是指在专利法在决定是否授予专利权时,具体检讨某项技术方案是否违背公共秩序、社会善良风俗的过程。如果该技术方案违背上述道德目标,专利法就应拒绝对其授予专利权。各国的专利法及一些国际公约中均有类似的规定。比如欧洲专利公约(EPC)中就明确规定当某项发明违背道德要求(Morality)破坏公共秩序(Ordre public)时,欧洲专利局(EPO)可以拒绝对某些技术方案授予专利权。善良风俗和公共秩序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在诸多部门法均如合同法、冲突法等中均有所涉及,可是都没有能对这些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社会对之分歧太大,实际上也不可能取得一致[43][43]。在著名的Greenpeace Ltd. v. Plant Genetic Systems N. V.(1995)案中EPO就认为,欧洲范围内关于Morality和Ordre public并无统一的定义,能够接受的说法是Ordre public涉及有关保障公共安全、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身体完整(the physical integrity of individuals as part of society)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而Morality则是指评价一些行为是否合适因而能被接受的标准,它植根于某一特定文化传统下的全部行为准则 [44][44]。根据这些模糊的表述,很难想象法官或专利局籍此来论证实施某一发明会确确实实第危及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不会在社会中引发争议。现在基因技术的专利问题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反对者当然不会放弃利用此类道德条款否定基因专利的机会。于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专利法中此类严格的道德评价条款究竟应不应该存在?
反对在专利法中设置较严格的伦理道德标准的学者有以下考虑[45][45]:
首先,专利权的获得并不意味着权利人就能够在工业上实际使用该项专利技术,相反,专利权人还要遵守其他社会强行法(如刑法、环境法等[46][46]),如果其他法律禁止某些发明专利的实施,专利权人依然没法行使其专利权。在现代社会中,为了维护生态安全及生物伦理,各国已经出台了许多有关基因工程、人体胚胎以及药物生产等法律法规。这些法规无疑起到限制权利人实施那些无法为社会所接受的专利作用,专利法应该保持其自身单纯技术色彩,没有必要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些原本由其他法律作出规定的道德原则。例如,世界各国关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立法基本就回避了此类道德问题,将之交由其他法规来判断,另外,UPOVC也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47][47]。
其次,专利法依据某些道德原则,拒绝对某些技术方案提供专利保护,并不意味着这些发明就一定无法实施,相反,不提供保护,就相当于此类技术处于公有领域,对任何人开放。由此看来,专利法并不是制止某些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伦理道德风险的有效制度,也就是说,依据专利法来防止科学技术的滥用是不可行的。
第三,一项技术只有具备实际生产价值后,申请人才会去申请专利。如果一项技术有违社会强行法,无法进行市场化,从而不具备市场价值,权利人就不会去申请专利保护。因此,即使在专利法中规定详细的道德原则,实践中也未必有多大用途--EPC第53(a)条及欧洲各国的有关道德条款在专利实践中很少被应用过。
另外,有人依据欧洲议会1998年6月通过了关于生物技术专利问题的指令,其中RECITALS[48][48]中将上述第一条理由演绎到极致,认为一项专利并非授权持有人实施该专利的权利,而仅仅是禁止第三方基于工业与商业目的使用该发明的权利[49][49]。专利权既然只是禁止竞争对手对该技术的使用,而不是赋予权利人实施权,自然不必在专利法中规定某项发明的实施违背公共秩序时拒绝授予专利权。
诚然,专利法具有浓厚的技术色彩,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其对保护对象进行道德或公共秩序评价的理由。同时,依据市场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想法是不可靠的---如果市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社会中诸多有关伦理道德的强行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上述理由有一定的道理,提醒人们要将专利法的公共秩序评价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我们不能因此彻底否定专利法中相应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专利权的获得依赖于国家的行政授权,在社会公众看来,权利人获得一项专利权,意味着国家公权机构对其技术成就的“嘉许”[50][50]。给予一项专利,其实就是从道义上对有关做法的一种支持[51][51]。此类嘉许与支持如果不含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判断标准,则有悖于我们的立法目的,破坏法律基础。因为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就是要设计一种机制来刺激有利于社会进步文化与科技技术的供给。这一目标中就当然地包含着社会道德伦理的价值判断,专利法要完全回避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对那些应用于社会明显会导致道德沦丧、公共安全受威胁等严重社会后果的技术,专利法当然不能对之给予专利保护。即使这种否定并不符合社会经济效率的要求,我们也不能放弃,因为人类总有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是不能放弃的。
二、 基因专利究竟是否能够经受住检验?
对基因专利保护持激烈反对态度的是绿色和平组织,他们认为,对人体基因申请专利,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奴隶主义(A modern form of slavery)[52][52] 。这只是一种误解:权利人对某一基因序列拥有专利权,只是单纯的商业竞争工具,用以防止竞争对手对之进行商业化使用[53][53]。权利人并不对他人及人类的人身享有任何权利,因而谈不上是一种新型的奴隶主义。
以上是从专利法立法目的的角度讨论专利法不保护科学发现的深层次原因,接下来我们回顾历史上相同问题在一些国家引发的争论。这种回顾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专利法对发现进行限制的真正原因。
1922年在欧洲的法国,J.Barthelemy 教授向法国 (The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废止关于禁止对科学发现等授予专利权的规定。在该建议中,他提出两点设想:首先,科学家可以获得所谓的原理专利(Patent of Principle),其保护期为有生之年加死后50年;其次,科学家作出某项发现以后,如果他人基于该发现作出某项应用发明,则科学家有权就该发明所获利益主张自己的分额。无独有偶,同一年,意大利的(the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最终批准了Bergson 教授的一项计划草案。在该草案中他说当时专利法对科学发现不给予专利权保护,The Whole Question is dominated by crudest utilitarianism ,empiricism unhappily disguised in scientific nebulosity ,and ,finally ,the most disconcerting arbitrariness .他说J.Barthelemy 教授的建议在法国没有被采纳,是因为法国人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接受该建议以前,如果法国单独对科学发现提供专利保护,则法国的工业将被迫支付比其他国家竞争者要多的许可费用,从而阻碍法国工业的发展。Bergson 教授因此建议,通过创设一项国际条约使各签字国共同来维护科学家的这项权利。这项建议走得相当远——当时(The League of Nations)的专家甚至还着手起草该公约草案。到了1930年,这一努力宣告失败,其结果是政府决定以政府奖励来代替科学专利,给予科学家以奖赏。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的发展,对科学发现进行政府奖励的做法逐渐得到推广。[36][36]学者们解释这一做法是列举了一些理由,比如很难追溯某项应用发明的科学根源、应用发明常常远在科学发现之后不便支付许可费、不利科学界的交流等等[37][37],其实专利制度对任何发明给予保护,都要面临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发明与发现上的表现并不会有质的区别。拒绝对科学发现给予专利保护如果还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的结果的话,那也是经过利益权衡后采取的完全实用主义的做法:不是发现本身固有的属性导致其不适合专利保护,而是发现作为基础研究的一部分社会不愿给予专利保护。在缺乏产业集团的游说的情况下,这一实用主义规则尽管不符合基础研究人员的利益,还是被专利法接受了。
在理论上和立法实践上,我们努力地区分发明和发现,将科学发现明确排除在专利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在司法实践中则应该解释为法院应该象Lord Justice Mustill 在 Genentech v. Wellcome 案中所说的那样——“在审查专利的专利性问题时,必须对该技术方案是否属于发明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即确定技术方案是一种发明以后,法院才能往下走”。 Lord Justice Hobhouse在Biogen v. Medeva 案上诉审中,同样支持这一观点,认为除非该技术方案是一项发明,否则任何权利要求都是无效的[38][38]。可是,在英国享有盛誉的HOFFMANN法官却否定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立法实践中,许多国家的专利法和国际公约中均没有对发明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选择变通的办法--通过约定一系列专利性条件来限定授予专利权的范围,比如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以及一些明确的排除性规定。在立法者看来,不能说不存在不是发明但依然满足上述要件的法案存在,但是至少立法者还没有想到一个例子。司法实践中,法官有时直接依据所谓的直觉就可以说某些对象是发现而不是发明,但是更多的时候,法官不能依据此类直觉,相反,他要求助于所谓的专利性判断[39][39],符合专利性的要求并被一些强行性规定所排除就应该受到专利法的保护。有人会说专利法中都明确将科学发现作为一种排除规定明确宣示,可实际上基因技术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的业已建立起来的法律概念体系,模糊了发明同发现的界限[40][40],甚至说根本就没有界限。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专利法的历史基础是机械和化工技术,而生物技术与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难以为现在的专利法概念所涵盖,[41][41]。这样,专利法对科学发现的排除规定基本对法官起不到什么作用,法官实际上是在依据专利性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对一项技术授予专利权,至于该项技术究竟是发明还是发现倒并不重要。
四、我们的结论:淡化发明与发现的区分,严格专利性审查标准
我们的专利法已经接受了自然物质的提纯物的专利请求,这实际上也使我们的专利法走上了同西方国家专利制度基本相同的发展道路,不可能独自偏离这一方向了。我们肯定了提纯物的专利性,那么与此相近蛋白质分子序列、基因序列等就注定要照此办理了。作为一种政策上的考虑,我们或许可以借此机会重新考虑自然物质的是发明还是发现的问题——本来应该在很早以前仔细讨论这一问题并适当坚持我们的意见。但是,如前文所述,我们认为专利法上对发明和发现的区分,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随着利益天平的倾斜,这一规则也会被直接或间接地被抛弃。我们简单地将这一规则视为不可退让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取的,以之来抵制我们不愿看到的专利法保护范围迅速扩大的趋势是不现实的。在现在国内国际的商业竞争的环境下,单纯的理论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真的显得很苍白了。
我们说专利法在处理基因序列之类的专利问题面前,淡化所谓的发明同发现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专利法应该立即将“科学发现不受专利法保护”这一规则清除出去。实际上我们已经基于这一规则将很多技术方案排除出专利法的保护范围。人们逐渐把这些排除规定当作公理而接受,如果突然改变这一规则,我们又要借助新的原则或规则来论证这些先前已经被排除的方案不应受到专利保护的理由,势必引起新的混乱。当然,这里蕴涵的假设是过去专利法对保护对象的界定是已经被现在的社会接受。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专利法只有在面对新的保护客体时,才需要重新利用新的原则来考虑问题,或者说抛开表面的规则来考虑问题——不必过分拘泥于发明同发现的区别,更多地关注其他专利性的审查。基因技术就是这样的新客体,没有必要先确定其是发明还是发现,而应直接对之审查三性,符合要求的自然应当授予专利。毫无疑问,我们忽略对发明还是发现的审查,不是因为我们不担心这种策略会给打破传统的发明人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而是我们认为在这些新的客体面前,发明与发现的区分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真正关注这一区分。抛弃过去的规则,是因为我们不愿在这里纠缠不清。为了尽量减小这种策略的消极影响,我们强调应该严格审查此类技术方案的专利性即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等,尽量避免那些缺乏产业实用性等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被垄断,从而防止专利制度成为社会技术进步的障碍。具体如何审查基因技术专利的专利性,这将在下一章介绍。
第二节 基因专利保护与公共政策
生物专利远在生物工程技术引人注目之前便已经存在:第一项有关生物有机体的专利是十九世纪中叶在芬兰颁发的。美国则与1873年对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颁发一项有关无机病原体酵母专利。另外,生物专利已经得到<<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斯特拉丝堡公约>><<慕尼黑公约>>的认可[42][42]。但是早期的生物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甚微,有关专利问题并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
如前所述,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人类开始利用基因工程手段随心所欲地改变周围的生物世界:下至微生物上至人自身,无一例外。此类技术直接影响到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生命对自身的道德观念,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另外,生物基因技术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所表现出的巨大威力,又加深了人们对其可能被滥用的担忧。这些关注和担忧,在专利法上就成为基因工程技术获得专利保护的阻力。很多人利用专利法中“违背公共秩序不授予专利权”的原则来反对给予基因技术以专利保护。以下就专利法中公共秩序等条款的合理性以及基因技术自身的道德性问题等展开讨论。
一、 专利法中的道德评价的必要性
专利法中的道德评价是指在专利法在决定是否授予专利权时,具体检讨某项技术方案是否违背公共秩序、社会善良风俗的过程。如果该技术方案违背上述道德目标,专利法就应拒绝对其授予专利权。各国的专利法及一些国际公约中均有类似的规定。比如欧洲专利公约(EPC)中就明确规定当某项发明违背道德要求(Morality)破坏公共秩序(Ordre public)时,欧洲专利局(EPO)可以拒绝对某些技术方案授予专利权。善良风俗和公共秩序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在诸多部门法均如合同法、冲突法等中均有所涉及,可是都没有能对这些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社会对之分歧太大,实际上也不可能取得一致[43][43]。在著名的Greenpeace Ltd. v. Plant Genetic Systems N. V.(1995)案中EPO就认为,欧洲范围内关于Morality和Ordre public并无统一的定义,能够接受的说法是Ordre public涉及有关保障公共安全、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身体完整(the physical integrity of individuals as part of society)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而Morality则是指评价一些行为是否合适因而能被接受的标准,它植根于某一特定文化传统下的全部行为准则 [44][44]。根据这些模糊的表述,很难想象法官或专利局籍此来论证实施某一发明会确确实实第危及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不会在社会中引发争议。现在基因技术的专利问题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反对者当然不会放弃利用此类道德条款否定基因专利的机会。于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专利法中此类严格的道德评价条款究竟应不应该存在?
反对在专利法中设置较严格的伦理道德标准的学者有以下考虑[45][45]:
首先,专利权的获得并不意味着权利人就能够在工业上实际使用该项专利技术,相反,专利权人还要遵守其他社会强行法(如刑法、环境法等[46][46]),如果其他法律禁止某些发明专利的实施,专利权人依然没法行使其专利权。在现代社会中,为了维护生态安全及生物伦理,各国已经出台了许多有关基因工程、人体胚胎以及药物生产等法律法规。这些法规无疑起到限制权利人实施那些无法为社会所接受的专利作用,专利法应该保持其自身单纯技术色彩,没有必要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些原本由其他法律作出规定的道德原则。例如,世界各国关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立法基本就回避了此类道德问题,将之交由其他法规来判断,另外,UPOVC也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47][47]。
其次,专利法依据某些道德原则,拒绝对某些技术方案提供专利保护,并不意味着这些发明就一定无法实施,相反,不提供保护,就相当于此类技术处于公有领域,对任何人开放。由此看来,专利法并不是制止某些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伦理道德风险的有效制度,也就是说,依据专利法来防止科学技术的滥用是不可行的。
第三,一项技术只有具备实际生产价值后,申请人才会去申请专利。如果一项技术有违社会强行法,无法进行市场化,从而不具备市场价值,权利人就不会去申请专利保护。因此,即使在专利法中规定详细的道德原则,实践中也未必有多大用途--EPC第53(a)条及欧洲各国的有关道德条款在专利实践中很少被应用过。
另外,有人依据欧洲议会1998年6月通过了关于生物技术专利问题的指令,其中RECITALS[48][48]中将上述第一条理由演绎到极致,认为一项专利并非授权持有人实施该专利的权利,而仅仅是禁止第三方基于工业与商业目的使用该发明的权利[49][49]。专利权既然只是禁止竞争对手对该技术的使用,而不是赋予权利人实施权,自然不必在专利法中规定某项发明的实施违背公共秩序时拒绝授予专利权。
诚然,专利法具有浓厚的技术色彩,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其对保护对象进行道德或公共秩序评价的理由。同时,依据市场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想法是不可靠的---如果市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社会中诸多有关伦理道德的强行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上述理由有一定的道理,提醒人们要将专利法的公共秩序评价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我们不能因此彻底否定专利法中相应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专利权的获得依赖于国家的行政授权,在社会公众看来,权利人获得一项专利权,意味着国家公权机构对其技术成就的“嘉许”[50][50]。给予一项专利,其实就是从道义上对有关做法的一种支持[51][51]。此类嘉许与支持如果不含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判断标准,则有悖于我们的立法目的,破坏法律基础。因为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就是要设计一种机制来刺激有利于社会进步文化与科技技术的供给。这一目标中就当然地包含着社会道德伦理的价值判断,专利法要完全回避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对那些应用于社会明显会导致道德沦丧、公共安全受威胁等严重社会后果的技术,专利法当然不能对之给予专利保护。即使这种否定并不符合社会经济效率的要求,我们也不能放弃,因为人类总有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是不能放弃的。
二、 基因专利究竟是否能够经受住检验?
对基因专利保护持激烈反对态度的是绿色和平组织,他们认为,对人体基因申请专利,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奴隶主义(A modern form of slavery)[52][52] 。这只是一种误解:权利人对某一基因序列拥有专利权,只是单纯的商业竞争工具,用以防止竞争对手对之进行商业化使用[53][53]。权利人并不对他人及人类的人身享有任何权利,因而谈不上是一种新型的奴隶主义。
网站创始人
- 个人简介:(学术)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
- 邮箱:fengxiaoqingipr@sina.com
-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
- 个人简介:(实务)
- 最高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首届研究员
- 中欧仲裁中心仲裁员
- 深圳、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 中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审判研究会知识产权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热点文章排行
联系我们更多>>

- 通讯处:(Zip:100088)
点击进入免费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