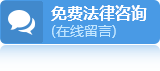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
来源:知识产权学术与实务研究网 作者: 时间:2006-09-16 阅读数:
|
作者特别说明: l 本文原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 页144-164,原发刊物对本文有所删节。 l 作者联系信息:崔国斌 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100084,guobin@tsinghua.edu.cn。 |
崔国斌
清华大学法学院
一、引言
在财产法领域,法官利用成文法法的原则条款或者普通法的宽泛学说创设新的财产权的造法活动通常都受到限制:很多大陆法系国家物权法将物权法定(Numerus Clausus )作为法律原则加以明确宣示;[1]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则事实上奉行这一原则[2]。究其原因,“物权法定”原则具有保证成文法的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等方面的功能,[3] 在各国具有普遍的价值。当然,在传统物权法领域,这一原则并没有被绝对化,存在一些例外。[4]只有这样,法律才可能保持一定的弹性,满足现实社会的特殊需要。
知识产权法上权利法定和法律弹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样存在,而且比传统财产法上的冲突更为激烈。一方面,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客体智力产品大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不因使用而耗竭,能够为社会公众所广泛共享。法院对于个人创造成果保护范围或者某些客体的范围的认定,对整体的社会成本和福利有着重要影响。[5]在智力产品上创设财产权,影响所及远远超过在有形物上创设物权。因此,知识产权法似乎更需要维护知识产权法法定原则,对法官的造法活动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需要直面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商业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新问题。知识产权立法也因此被认为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无法对这些新问题做出及时回应。[6] 于是,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官造法现象在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地存在。比如,在美国法院可能依据普通法判例中确定的“非法盗用学说”(Misappropriation Doctrine)对联邦立法保护范围之外的一些知识产权客体提供保护,比如实时新闻、名人形象、未出版的作品等。[7]大陆法系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造法活动与英美法国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官常常对民法典或者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的原则条款进行扩充解释,将知识产权法的实际保护范围向外拓展。[8]比如,德国司法判例就广泛适用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对知识产权法不保护的客体提供补充性的保护。[9] 法国也是如此。[10]
有研究认为,法院适用民法或者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禁止竞争者未经许可利用他人创造的知识产品,并非创设新的独占性的财产权,仅仅是在禁止某种竞争行为。[11]从理论上讲,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保护与绝对的财产权保护,有一定的差距。[12]但是,法院对于所谓的“竞争关系”或者潜在市场作非常宽泛的解释,最终导致法院所谓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与知识产权的财产权只是量的不同,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是给同一事物贴上不同的标签而已。[13]对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构成实质性影响的行为,绝大多数都可以解释为广义上的竞争行为。因此,本文在后文中不再刻意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保护与传统意义上知识产权保护的差别。
本文尝试在中国的语境下,对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与保持知识产权法的弹性的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继承了大陆法系的传统,缺乏判例法制度,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官造法活动本该持严格限制态度。但是,中国的学者实际上更强调维持知识产权法的弹性,鼓励法官利用法律的原则条款拓展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国内很多学者认为这是法院弥补现有法律不足的有效办法,甚至认为这是立法之前的摸索范例。[14]在这一理论认识的鼓舞下,中国很多法官忽略学者在民法基本原则能否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方面的争论,[15] 利用《民法通则》、《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原则条款,不断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类型、拓宽解释知识产权的权能、甚至直接否定知识产权法成文法规则。
本文对中国法院的造法活动进行批评,希望重新确立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在中国司法活动中的统治地位。本文首先通过具体案例揭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法官造法的具体表现,然后分析了造法活动所折射出的 “自然权学说”的权利观。正是受这一权利观的影响,中国法官在大陆法的传统下对造法活动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本文认为这一权利观违背中国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背离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从而将部分法院的司法活动引入歧途。接下来,本文具体分析了法官造法活动对成文法造成的现实危害:否定立法政策,打破法定的利益平衡,威胁公共领域的行动自由和法律的统一性,并可能为国际保护打开后门。最后,本文指出为了维护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避免司法造法活动泛滥,应当清除司法活动中的自然权学说的不良影响,限制法院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幌子下宽泛解释劳动者对其智力产品的控制权,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在极端例外的情况下,适用原则条款也应当谨慎对待所谓“市场失败论”,将造法活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二、中国法官的造法活动
(一)扩充保护客体的范围
中国诸多法院在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先后利用法律原则条款在判决中确认商品装潢、不具备原创性的数据库、未注册商标、域名、未保密的技术成果受法律保护。尽管法院在这些案例中的判决未必是终局性的,但是透过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部分法院在适用法律原则条款上的一贯思路。
(1)商品装潢。在1989年莒县酒厂诉文登酿酒厂案中[16],被告在其生产的白酒产品上使用了与原告产品相似的瓶贴装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被告这一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民事权益”。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四、五条、七条等原则性的规定。本案判决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尚未出台。当时中国没有关于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的保护的规定。因此,本案被视为中国法院适用法律原则保护商品装潢的开创性案例。[17]
(2)没有原创性的“作品”。在著名的1994年广西电视节目表案例中[18],原告基于其和中国电视报社的协议取得在广西境内刊载《中央电视台节目预告表》的权利。被告未经许可刊载该电视节目预告表,因此引发争议。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电视节目预告表是否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终审法院“电视节目预告表不具有著作权意义上的独创性,不宜适用著作权法保护。”[19]但是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确认权利人对节目表享有一定的民事权益或者说财产。
这一案例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也得到国内学者的支持。[20]通常认为,这是法院在缺乏数据库保护专门立法的情况下,主动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延伸到数据库的代表性的案例之一。[21]在后来的一系列案件中,法院大多认为此类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应当受到保护,只是适用的法律条款有所变化。[22]
(3)域名。域名本身在国内知识产权法上并非直接的保护客体类型。[23] 但是,在2001年10月的中项网、2002年12月“51job”域名纠纷等案中,法院又都直接承认域名之上会直接产生一种民事权利,并受保护。[24]法院的这一立场似乎受最高法院2001年年
(4)未注册商标。我国商标法奉行注册保护原则,没有注册的商标通常不能获得商标法上的保护。[27]对于未注册的驰名商标或者知名商标则存在一定的例外。[28]对于未注册商标不给予保护,“法院有时感到实在不公平,只好在《商标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外找间接的原则去判案。”[Page][29] 比如,在北京市东城区景山炉灶曹维修服务部诉北京育德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一审判决案中,法院就承认商标的先使用人享有民事权益,依法受到保护。[30]国内也有诸多学者支持法院对未注册商标提供法律保护。[31]
(5)未保密的智力成果。在1995年北京仪表机床厂诉北京汉威机电有限公司案中, 一审法院在明确原告“仪表厂主张的商业秘密未能满足法律规定商业秘密必备的要件,都不能作为商业秘密给予保护。” [32]但是,法院依然认为被告雇佣其雇员并获取相关技术知识的行为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第4条)和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法院认为被告聘用仪表厂员工,利用其掌握的同类产品的信息为自己服务,减少了自己在寻找、取舍、确定制造专用生产设备厂家和外协加工单位所应付出的劳动,节省了时间。这些行为都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违背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应当受到法律的规范和制裁”。[33]参与该案审理的法官在二审法院否定一审判决意见后评论该案时依然坚持一审的意见。[34]该法官的意见显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前面提到的青岛天气预报一案中,法官实际上也持有类似的思想——认为天气预报信息作为一种技术成果,即使在公开后依然受到保护,他人不得利用。[35]在广东省高级法院判决的宋维河诉东北菜风味饺子馆不正当竞争一案中,法院也认为设计师设计的对外公开的饭店的整体风格属于智力劳动成果,尽管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获得保护。[36]
(二)扩充知识产权的权能
中国法院还会利用不正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一些原则条款,扩充某些知识产权的权能,为权利人提供超出成文法范围的保护。比如,法院先后确认过商标权人禁止反向假冒的权利,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等。
(1)禁止反向假冒的权利。在北京市京工服装工业集团服装一厂诉北京百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等案中,被告同益公司从公开市场上购买了原告“枫叶”牌服装,然后撕下“枫叶”商标,贴上“鳄鱼”商标对外销售。[37]本案争论的焦点是被告撤换原告商标——即所谓的反向假冒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据当时的《商标法》,商标侵权行为基本上限制在利用与注册商标相同和类似的标志的范围内。[38] 《商标法》并不赋予商标权人以积极的保证其商标必须附着在其商品上的“积极权利”。[39] 法院在民法和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条款的名义下,[40]为商标权人创设了一项新的与先前商标权有着质的不同的权利——那就是未经许可不得揭掉商标标志的积极权利。
(2)信息网络传输权。在著名的“王蒙等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案”中,[41]被告未经许可在网站上上载了原告作品,法院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网络传输行为的著作权法规范。当时的著作权法并没有像2001年修正后的著作权法第十条那样规定所谓的信息网络传输权,[42]于是一审和二审法院均“开创性”地解释了法条中的“等”字,认为“网络传输权”是著作权的一项权能。这一案例也因此成为中国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经典案例,倍受国内学者的好评。最高法院在2000年的司法解释中也确认了这一案件的结论。[43]《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公报》后来公布这一系列案件中的一个。[44]
(三)否定现有的法律规则
中国法院的造法活动最为极端的表现就是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直接否定现行成文法规则。比如, 2002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直接规定,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委托他人创造自传体作品,著作权归当事人(委托方)所有。[45]最高法院刻意使用了“合意”,而避免适用“委托”、“合作”一词来表述当事人和创作者之间法律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属于典型的委托或者合作创作关系。依据中国著作权法,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著作权应该由受委托方(创作者)享有或者合作方共有。[46]最高法院做出上述司法解释可能与先前困扰法院的“末代皇帝”的《我的前半生》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有关。[47]最高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直接否定了著作权法关于委托作品或者合作作品著作权归属的明确规定,已经不是释法而是地地道道的修法了。这类造法活动明显超越法院职能,其错误不言而喻。后文不再对此类法院“修法”活动作任何讨论,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提到的扩充保护客体和知识产权权能两类造法活动上。
三、法官背离知识产权法立法思想
(一)不同的知识产权观
中国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对创设新的知识产权的开放态度,与法院所接受的知识产权权利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具体分析中国法院的知识产权观之前,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知识产权领域两种对比鲜明的权利观的学说:劳动自然权学说和功利主义学说。[48]
所谓洛克式的劳动自然权学说,大致如下:上帝将整个世界赐予人类,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继而对自己的劳动享有所有权。当其将劳动添加自然物上,人便获得该物的所有权。[49]洛克的劳动学说有着深厚的自然法思想渊源。[50]后世学者们试图将洛克的学说精确化,期望按照一个严密的逻辑来验证财产权制度的合理性。遗憾的是,不同的解释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以致人们会怀疑二者是否在谈论相同的文本。[51] 不仅如此,还有学者直接质疑洛克理论自身的逻辑。比如,诺齐克(Robert Nozick)提出的著名的“番茄汁”的例子。[52]不过,广泛存在的争论和质疑并没有影响到洛克理论的社会影响力。劳动学说对于财产权制度的影响,同其理论自身的精确性、逻辑严密性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劳动学说的威力来源于人们直觉性的接受和遵从。[53]
洛克的劳动学说,最初所描述的财产客体无非是麦子、果实之类有形财产。但是,在“大脑劳动的产物等同于双手的劳动成果”的观念下,[54]后来的学者则很自然地将它应用于知识产权的合理性论证上,认为劳动者对其付出劳动创造出的智力成果享有当然的支配权。不过,象传统的财产权权领域一样,知识产权领域也继续重复着传统财产法领域无休止的“正当性”的争论。[55]
所谓功利主义财产权学说,主要源于休谟(David Hume)和边沁(Jeremy Bentham)。[56]休谟认为我们所遵循的正义规则来自那些被认为有利于促进人类幸福的一些习俗(Convention)。人们遵守这些规则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同时自然也有利于公共福利。私人所有权及其规则的基础除了这一实用目的别无其它。[57]休谟之后,边沁更明确的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然权,财产权完全是法律的人为创设。[58]具体到知识产权,功利主义认为社会提供知识产权制度的终极原因是为了提供刺激动机,以扩大相应成果的供给,保证社会公众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产品。[59]在版权法领域,“版权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给予作者回报,但法律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它的最终目标--促使其将其创造的天才的产品公诸于世。[60]对于专利系统,功利主义的解释更是直接:专利只是经济政策的一个公共工具,有着两方面的功用:首先是提供刺激动机,刺激有实用性的发明创造不断涌现,从而导致社会福利的增长;其次,专利制度本身构成一个完备的信息系统,促进整个社会的技术信息的迅速传播,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开发,从而减少社会财富的浪费[61]。
自然权学说和功利主义学说对知识产权法的司法适用有着不同的影响。在自然权学说的影响下,知识产权法更倾向于忽略保护知识产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62]重心更倾向于保护创造者的劳动成果。任何妨碍权利人实现其劳动成果的市场价值的行为,都有可能依据知识产权法、民法等法律规则或者原则被禁止。而功利主义学说的默认规则不是保护,而是不保护。在缺乏明确法律规则的情况下,一切智力成果一旦公开,就进入公共领域。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使用,没有特别法的禁止都是许可的,即使这种使用给权利人造成强有力的竞争压力,损害其商业利益。在这种思想理念中,公共领域无所不在,权利人控制的区域不过是公共领域中特区而已。[Page][63]
对造法持开放态度的部分法官实际上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受了劳动自然权学说的指导。[64]在前面提到的诸多案例中,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法院习惯于将劳动创作活动作为确认创作者对该劳动成果享有财产权或获得法律保护的基础。[65] 法院本着“保护劳动所得和合法所得不受他人侵犯”的“民法之基本精神”,[66] 将“劳动者对其创造的劳动成果有当然的控制权”确定为一项公理性的法律原则。法院在具体案件中会因为适用法律的不同,给这一“劳动者控制劳动成果”的原则穿上不同的外衣:如果适用民法的原则条款,则可能被表述为“诚实信用原则”、或者“合法的民事权益受到保护”;如果适用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则常常被表述为“正常的商业道德”。[67]
“劳动自然权学说”有着直觉性的号召力,中国很多法官深受这一学说的影响,并不奇怪。但是,“劳动自然权学说”并非中国知识产权法立法的主导思想。相反,功利主义在中国立法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接受自然权学说的指导,很容易背离立法者确立的立法政策。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揭示中国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指导思想。
(二)中国立法中的功利主义
中国知识产权法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值得称道的历史传统。[68]现行知识产权法诞生之时,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劳动者当然享有其智力成果的社会共识。这些立法得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改革开放的外部需要,而不是主要源于社会内部自然权利意识的凝聚。[69] 立法之时,中国在政治生活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指导。虽然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具有深厚的自然法渊源,[70] 但是马克思却凭借劳动价值论对私有的财产权进行了系统地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政治图腾时,不但没有在中国培植出自然权的主流意识,甚至导致著作权之类的私权被彻底否定。[71]
中国知识产权法并不是孕育在一个象传统欧洲那样富有自然法传统的社会环境中。[72]中国的立法者制定知识产权法为智力成果提供保护,并不是出于对所谓自然权学说的默认规则的尊重,[73]而是出于一系列功利主义的考虑。比如万里同志在《专利法》立法前关于该法立法目的阐述就非常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当时认为专利法的立法目的有三点,“其一,便于发动大家搞发明创造;二是便于迅速推广应用技术发明;三是便于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74] 从这一典型的表述中,我们就丝毫看不到自然权学说的影子。中国专利法的立法过程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政策权衡。[75] 政策性权衡的结果直接体现在当时的《专利法》中。比如,该法的第25条就出于国家政策的原因明确将食品、药品等客体排出专利法的保护范围。[76] 中国版权法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政策性权衡,这里不再赘述。[77]
中国知识产权法不是对强调保护个人成果的自然法规则的确认,而是在“知识共享和自由竞争的主流规则”之外创设的特殊规则,在原本毫无知识产权观念的社会中创设一些法律禁区,为权利人提供有限的保护。中国的立法者就像当年美国国会那样选择了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 “制定版权法是创设了权利,而不是确认已经存在的权利;” [78] “不是基于作者的自然权利,而是基于公共利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79]
中国立法者所选择的功利主义指导思想,在中国当今社会中依然存在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先前中国社会围绕盗版软件终端用户的法律责任所展开的激烈争论中略见一斑。表面看来,终端用户在安装盗版软件的时候,大多要进行复制从而侵害软件权利人所享有的复制权,因此按照现行的著作权法追究终端用户的侵权责任不成问题。[80]可是,中国社会却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纯粹的政策性的意见取得了优势。[81]最高法院在新的司法解释中实际上迎合了这一公众意见。[82] 本文无意对这场争论的是非做出评判,只是想通过这一案例说明:中国社会公众远远没有将版权视为创造者的天然的一种权利。中国社会的知识产权理念依然是功利主义的,更愿意将知识产权法视为一种政策性的规则。不仅在个案中如此,中国社会在讨论其它重要的知识产权议题时,也同样习惯于按照功利主义的思想去进行规则的取舍,而不是在追求某种自然法上的权利。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社会公众所期待的立法基调依然是推崇知识信息的共享,推崇模仿以促进竞争。鲁迅时代的“拿来主义”依然是中国社会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知识的主导思想。中国还远远没有到达可以以保护主义当头的时代。
中国立法者从整体上选择了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并不妨碍著作权法在某些微观制度环节上引入了欧洲大陆的一些极富自然权学说或者人格学说色彩的制度规则,比如著作精神权保护制度等。[83]中国的立法者和国内学者似乎认为著作权精神权并不对现实生活中作品的利用构成现实的威胁,因此毫不吝惜地给予无期限的保护。[84]不过,中国在移植这些带有欧洲大陆色彩的规则时,低估了此类权利对于作品自由利用的潜在影响。禁止作品被歪曲、保护作品完整权可能被利用来限制后人自由改编、演绎处在公共领域的作品,成为私人审查的工具。[85]
(三)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的观念冲突
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者选择功利主义,而司法者执着于自然权观念。中国法院之所以在知识产权法审判活动中倾向于选择自然权学说的默认规则,与中国民法学说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在大民法的体制下,将知识产权视为民事权益的一种,习惯了将知识产权客体与普通民事财产客体等同起来的思维模式。而中国的民法学说和制度直接从欧洲大陆移植过来,有着深厚的自然法传统。[86]自然权学说所体现的是一种个人本位的传统财产法理念。[87]比如,劳动权利说强调的是个人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人格权学说则强调财产权旨在完善个人的人格发展等等。自然权学说并不十分关注财产权对社会公益的影响。[88]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深受自然权学说影响的“欧洲大陆的知识产权体制更强调保护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强调促进公众获得艺术享受的长远利益。”[89]
知识产权客体与传统有形的财产权客体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别。知识产权客体因其无形,而具备了与传统财产权客体显著不同的公共物品属性及无损耗属性。[90] 无形的信息资源在同一时间可以由无数人共享,而不减损其使用价值。
“与侵占物理财产不同,侵占信息或者其它无形财产通常并不剥夺原始使用者同时使用的机会。在无形的有价值的商业信息上设置独占权利,会妨碍竞争者接触该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损害竞争,也堵塞了公众充分利用有价值的思想和创意的渠道。”[91]
法院赋予一种无形客体以垄断权时,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远远超过法院确认某一种有形财产。[92]正因为如此,知识产权法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逐步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93] 知识产权法比传统民法更强调维护信息自由,更强调权利限制,更强调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在知识产权法中,维持公共领域的自由开放,保证社会成员对信息的充分接触和利用,甚至比传统社会中保障个人对有形财产的掌控更为重要。
中国法院接受传统民法学说的指引,更倾向于按照自然权学说的理解来解释知识产权规则。在司法活动将信息产品与有形物类比,忽略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从而很容易对信息产品的过分的保护。[94] 知识产权法和传统民法的冲突,本质上是个人本位的财产观与社会本位的财产观的冲突。现代民法虽然存在着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过渡的趋势,[95]但是在时下的中国显然远远落后于知识产权法的脚步。如前所述,中国的立法者实际上选择了社会本位的功利主义的知识产权观。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该像美国法院那样抛弃传统民法领域的自然法的立法思想,努力维护功利主义知识产权观在司法活动中的统治地位。[Page]
四、法官造法泛滥的现实危害
(一)违背知识产权法基本原则
在知识产权法对某些客体不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法院在利用原则条款造法提供延伸保护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行知识产权拒绝保护这些潜在客体的真正原因。如果现行知识产权法恰好是为了维护某些至关重要的立法政策才拒绝对这些客体提供保护,则法官的造法活动将危及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损害知识产权法所刻意维护的公共政策。在前文提到的“广西电视节目表”等案例中,法院的造法活动中就出现这一问题。
版权法存在这样的一项基本原则:版权保护不延及事实和思想。[96]版权法确立这一原则,有着非常明确的立法目标:单纯的事实和思想的自由交流对于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的个人所垄断将会严重的限制后来者的创造自由。[97] “原始事实可以随意拷贝……,这正是版权法促进科学进步的手段。”[98]对社会公众而言,自由拷贝是法律赋予一种权利。[99]因此,版权法拒绝对思想和事实提供保护,并非有意将这些内容的保护留给其它法律(比如中国法院所理解的民法或者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而是版权法认为基于既定的社会公共政策,这些客体本来就不应该获得法律的保护。就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Feist案中所说的那样,拒绝对此类客体提供保护好像不公平,但这不是成文法的未曾遇见的负面结果,相反,正是版权精髓的体现。[100]
中国法院在广西电视节目表、霸才数据信息等案对不具备原创性的“作品”提供替代保护,[101]表面上是利用原则条款在填补法律的空缺,实际上是在否定著作权上的基本原则,否定维持公共领域自由开放的重要性。版权法强调事实和思想的自由利用,拒绝保护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作品,或许真的会导致数据库类作品的供给不足,因而有可能需要修正版权法这一原则,将数据库作为例外进行特殊立法保护。[102] 但是,这一法律调整将对社会的公共生活和产业竞争产生深远的影响。[103]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缔结相关条约时,各国持谨慎的态度,最终导致拟议中数据库条约流产。[104]中国法院在立法者为版权法基本原则设置例外之前,就突破这一原则将知识产权保护延及没有原创性的“作品”,实在是草率。
除了数据库类的客体以外,中国法院还通过原则条款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延伸到未注册商标、未保密的技术、未注册的外观设计等客体上。法院在这些案例中判决同样威胁到现行商标法、专利法的立法政策。
首先,以未注册商标为例。中国商标法保护商标法的基本原则是注册保护原则。[105]法院确认经营者对其投入实际使用但没有注册的非驰名商标以所谓的“在先权”,可以对抗在先善意注册的商标权人。[106]这实际上违反了商标注册保护原则的基本价值取向,降低了经营者注册商标的紧迫感,同时也损害了注册体制本身的确定性以及权利人的正常预期。中国现行的商标法上并没有所谓的“在先使用”的侵权例外。在他人善意注册商标后,在先使用者继续使用该商标显然构成商标法第52条意义上的商标侵权行为。法院基于民法或者不正当竞争的原则确认先用者所谓的“在先权”,等于否定了商标法所做出的明确结论。
其次,未申请专利的技术成果。专利法实行强制申请原则。发明人或者设计者未申请专利就对外公开其技术方案或者产品外观设计(产品包装装潢),则该成果当然进入公共领域。法院在所谓的不正当竞争的名义下,限制竞争对手采用公共领域的技术成果或者设计方案,[107]则违背专利法上的强制注册原则。如果当事人能够在专利法之外轻松地利用法律的原则条款为自己的公开技术寻求保护,那又何必花费人力物力寻求专利法保护呢?[108]正因为如此,美国严格限制州法律对非商业秘密的公开技术提供替代性的保护,以防止联邦专利法所维护的上述政策受到损害。[109]在版权领域也是如此。[110]
本文认为,中国法院要避免上述违背知识产权法基本原则的造法活动,就必须摆正自己的角色: “法院不是立法机构,他们的任务不是宣布一项新的规则或者制定新的政策,而是在一项既定政策指引下,根据案件的所有细节决定具体的结果。” [111] 法院在决定对一项新的客体提供延伸保护之前,必须认真分析并充分尊重现行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和既定立法政策。法院不能在所谓的原则条款幌子下面,擅自否定成文法的这些原则,肆意拓宽知识产权法的客体范围。
(二)破坏法定的利益平衡关系
本文在前面的案例中,已经指出法官造法活动不仅表现在拓宽知识产权法保护客体范围上,同时还体现在创设新的权能上。法院通常将现行成文法解释为赋予权利人对某些客体以全面而周密的控制权。[112]当某项行为对权利人的全面控制权构成挑战,却无法依据成文法赋予的具体权能寻求救济时,法院就会在成文法原则条款的名义下,创设新的权能将这些法外的利益纳入权利人的控制范围。
法院在造法活动中所描绘的知识产权权能体系与功利主义立法者实际创设的权能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知识产权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是由成文法赋予的一系列单项的权能组合起来的。所谓的权能,对社会公众来说则是一种代价。立法者经过审慎的政策性权衡,将社会付出的代价限制在维持创造者正常的再创作的动力的范围内,从而建立知识产权法精细的利益平衡机制。[113]在此范围之外,社会没有必要为作者或者投资人提供额外的回报。这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法上的权利虽然是一项项法律具体赋予的明确的权能的总和,但是法律并不承认权利人因此对智力成果享有的笼统的、全方位的支配权利。比如,中国著作权法在赋予权利人复制、发行、改编等一系列具体权能之外,就没有普遍承认作品的进口权、功能性使用权、出租权、追续权、收回作品权、作品形象的商业化权等等[114]——尽管后面这些被“遗漏”的权能从形式上可以视为作者对作品的控制权。立法者的基本思路是:在没有这些权能的情况下,著作权法已经实现了权利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
在前面提到的王蒙案中,法院对著作权法中的“等”字进行扩张性的解释,从中创设出一种新的权利,即后来所说的“信息网络传输权”。[115]法院关于设立此类权利的必要性的解释也许有一定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违背立法精神径自创设此类权利。否则,法院完全可以依据同样的逻辑将著作权的权利内容扩展到所谓的出租权、进口权、作品形象的商业化权、作品标题的控制权等等。这样一来,著作权法通过一系列精细的制度安排所建立起来的利益平衡关系就可能被法院轻易打破。在王蒙案件中,当时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发行权”两类权利就可能为权利人提供有效救济。[116]退一步,当事人还可以选择所谓的共同侵权规则来追究网络内容提供商的责任。[117]在这种背景下,法院依然拒绝适用现有的规则,执意创设新的权利,更加缺乏正当性基础。[118]
法院在商标侵权案例中,也同样存在拓宽商标权权能的行为。比如,前面提到的 “反向假冒”的案例。[119]当时中国商标法上的判断商标侵权的基本标准是“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120] 也就是说,商标权人仅仅享有禁止他人使用其商标的消极权利,并没有保持其商标与商品之间联系的积极的权利。在“反向假冒”案中,法院恰恰是利用法律的原则条款确认商标权人享有这种超出商标法范围的积极权利。也许,真如学者所说的那样,当时的中国真的需要像国外其他国家那样立法确定禁止反向假冒,[121] 后来中国的商标法也的确做出这一规定,[12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越俎代庖,为商标权人创设新的权利内容,确立一项对现有市场竞争秩序发生深远影响的新规则——这一判决如果得到实际执行将对中国国内各行各业广泛存在的分装销售业务产生重大影响。[Page][123]
法院创设新的知识产权权能打破现有利益平衡关系的同时,并没有相应机制来消除同步出现的负面影响。法院不能像立法机构那样在知识产权立法过程中,调查、收集和研究各个利益群体的意见,难以对每一类客体所牵涉的权利人、社会公众、国家产业政策乃至国际竞争利益等问题全盘考虑以确立平衡的法律制度。[124]“法院也不能象立法那样设定一个武断的权利保护期限、不能创设一个行政机构或者公共注册机构以平衡各方利益、不能创设实体性的机构。”[125] 以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的保护问题为例。成熟定型的保护机制对数据库保护条件、保护的期限、合理使用等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希望借此实现公众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126]而中国法院所确认数据库保护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入门条件、没有保护期限、没有合理使用之类的权利限制……。[127]很难想象,中国这样的数据库保护制度是一种平衡了各方利益的理想法律制度。
(三)损害知识产权法的确定性
在知识产权领域,明确的预见性比传统的财产法领域更重要。在处理有形财产时,人们能够通过自己感觉有效把握该财产的物理边界,但是在知识产财产上这一感觉不复存在。[128]“知识财产的边界非常的模糊,人们非常容易侵害这些无形的财产。有时连专业的法律意见也不能为行为人提供明确的指导。如果存在利用模糊的原则条款创设权利的可能性,则加剧了法律的不确定性。”[129]正因为如此,知识产权法总是尽力让权利人的竞争对手能够清楚地了解权利的边界,从而对各自市场行为的法律后果有一个明确的预期。[130]比如,专利法要求申请人提供详细的权利要求,明确其权利界限,超出这一边界就是自由竞争机制的领地。[131]
法官利用“诚实信用”、“遵守商业道德”等抽象而模糊的原则创设类似财产的权利,则会打破知识产权法所努力维护的法律预期。社会公众每天不断地接受和利用各种各样的来自他人的思想、知识和信息。这些思想、知识和信息中都或多或少凝聚着创造者、收集者、传播者的劳动和智慧,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可以想象,社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可能动辄得咎,无所适从。现有的知识产权体制给公众所描绘的生活场景本来是:知识产权法仅仅是在自由竞争的公共领域创设了一些权利的孤岛。[132]在这些孤岛外,公共领域几乎是一片自由竞争的海洋,其中的任何可接触信息都是可以自由利用的。[133] 在法官造法的威胁下,自由竞争的公共领域倒可能成了孤岛,剩下的全是权利的海洋。
在社会公众看来,抽象的法律原则导致公众丧失行为的预见性。对法官而言,这些抽象的原则同样是漫无边际的。[134]不同的法院在类似的案件中对法律原则条款的解释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从而严重损害了知识产权法的统一性。比如,在前面提到的域名[135]、商标先用权[136]、未保密的技术[137]等问题上,中国法院不同地区的法院、上下级法院之间就经常出现完全相反的判决结论。
如何克服知识产权领域法官利用原则条款断案的不确定性,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支持更大的范围内适用“非法盗用学说”(法官造法的学说依据)的学者,为约束法官行为提出一系列的复杂限制条件。[138] 或许,在一些具有判例法传统的国家,法院可以在在先案例中将这些规则固定下来以约束后面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判决的确定性和统一性。[139]不过,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提出的权衡因素依然是模糊而粗糙的。依据这些权衡因素,法官的判决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判决的巨大不确定性。[140]在中国,消除判决法官造法的不确定性的难度更大——中国不存在判例制度,在立法者采取措施之前,建议中的方案没有统一适用的空间。因此,更明智的做法依然是严格限制法官造法。
在谈到法律确定性时,有学者强调知识产权法领域本来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需要法官个案裁量,比如专利技术的创造性、商标的描述性、作品的原创性、作品的思想和表达的二分等等。因此,知识产权法似乎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法律的确定性。[141]这实际上是以知识产权法部门法内部制度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为维持知识产权法整个制度框架的不确定性辩护。本文认为,确立无形财产权之后围绕权利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与是否存在无形财产的不确定性有着质的差别。如果无视这一差别,法律似乎就没有必要维护所谓的确定性的基本价值了。
(四)打开国际保护的后门
中国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件中肆意扩充解释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为国外的权利人打开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后门,危及中国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巴黎公约》、世贸组织的 TRIPs等重要国际公约中均规定了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容。[142] 由于这些国际公约的相关条款还非常的简略,因此,不正当竞争法的国际保护水平取决于各国国内法。外国权利人依据国民待遇原则享有与国内权利人同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143]中国法院在个案中对此已经予以确认。[144]
中国法院提供宽泛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导致外国人无需通过国际谈判、签署公约,就能够在中国获得知识产权方面的替代性保护。以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保护为例。依据现行的国际公约,中国并没有必要为外国的此类数据库提供特殊保护。[145]中国的数据库产业非常落后,在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146] 中国理当在数据库的国际保护保护上采取谨慎态度。[147]但是,如前所述,在广西电视节目表案之后的一系列案件中,法院却毫不犹豫地将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延伸到数据库保护上。[148]这也就意味着外国权利人也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中国寻求数据库的保护了。在美国及国际社会在数据库保护问题上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的法院就早早地给如此重要的政策性问题下了结论,而且后续的法院还在不断重复这一结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中国学者深思。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中确定保护范围的一些重要条款通常都比较宽泛。各国法院具体案件中对国内法以及这些公约条款的解释,直接关系到公约实际的保护范围。比如TRIPs协议中第27条关于专利法保护的技术客体的范围的规定看上去就非常宽泛。[149]如果国内法院接受自然权学说的指导,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持宽松的态度,很容易导致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的扩张。比如,生物工程、计算机程序等领域的一些新型客体——基因、程序算法、商业方法等,无一不是天才式的劳动和密集资本结合的产物,具有极大的市场价值。受自然权学说的影响,法院将很难拒绝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原则进行延伸保护。可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基于产业政策的考虑,尽量对这些新技术客体的保护保持低调,在缺乏国际公约约束的情况下尽量拖延立法保护的时间表。因此,法院在司法活动过程中谨守功利主义财产观,不轻易利用原则条款对知识产权法进行拓宽解释,对于落实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面,中国法院应该像美国最高法院那样,养成回避问题的良好习惯,将政策性取舍的重大问题推给立法者,而不是尝试着自己解决。[150]
五、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
在对中国法院的造法活动提出系统批评之后,本文接下来从正面阐述中国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活动过程中应当坚持基本指导思想,全面落实知识产权法定的基本理念。首先,要否定所谓的劳动学说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支配地位,确立功利主义财产观;其次,严格限制民法和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原则条款的兜底适用;最后,极端情况下适用原则条款,也要慎重对待所谓的“市场失败论”。
(一) 拒绝劳动自然权学说
中国社会私有财产神圣的基本观念还不够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劳动学说可能被视为有效的激发财产权神圣感的催化剂,用来抗衡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强调权利社会化的倾向。[Page][151]在传统的财产法领域,中国也许真的需要借助于个人本位的劳动学说这一朴素的理论的号召力促进公众对私有财产权的普遍尊重[152]——尽管对财产权的尊重并不必然要与劳动自然权学说挂钩。[153] 但是,将劳动学说延伸到知识产权领域,将有形物和知识产品画上等号之前,则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前文所述的中国知识产权法的传统、知识产品与生俱来的共享属性、知识财产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国际产业竞争等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中国的立法者没有接受很容易将劳动和产权联系起来的劳动自然权学说,[154] 而是选择了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相应地,中国法院也应当在司法过程中坚持功利主义地指导思想,有效遏制自然权学说所激发的知识产权扩张趋势。
司法活动中放弃劳动自然权学说,首先要强调智力成果的创造过程的社会性,打破自然法观念中劳动和产权之间的自然联系。“支持作者对作品控制权的最简单最直接的理由通常是:如果不是作者,作品就不会产生,因此保护其垄断权,也不会剥夺任何所获得的已有利益。”[155]其实,
“智力成果并非智力活动的凭空创造。考虑到后人对前人的智力成果的依赖,完全可以说智力成果是一种社会产品。即使智力成果的价值完全来自于人类的劳动,那也不能完全归功于某一特殊的劳动者。将个人的贡献从社会、历史背景中区分开来,简单地将智力劳动成果的市场价值归功于劳动者个人,忽略了其他人的历史贡献。”[156]
就象福柯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作者创作而获得所有权的规则,并非源于自然法,而是社会自行创立的用来分配作品所有权的一种人为规则。[157]也就是说,现代知识产权法之所以确立起发明人或者作者“崇拜”的意识形态,将产权赋予特定的个人,不过是为了解决产权归属矛盾,促进知识产权的立法目标的一种策略而已,并非对创造者自然权利的一种确认。基于同样的道理,法院也不应轻易接受劳动者应当收获其劳动成果的观念。在现有的法律规则之外,社会并没有设定“创造者一定要获得适当回报”的潜规则。[158]
司法活动中放弃劳动学说,还应该清除获取和利用他人智力成果的道德抵触感。西方社会在全球推行知识产权制度的过程中,将发展中社会的很多学习、模仿的竞争行为描述成偷窃乃至海盗行径,有意识地将人类传统的知识共享习惯“妖魔化”,给知识产权制度披上很强的道德外衣[159] ——尽管社会公众对智力成果的共享行为同杀人越货的海盗掠夺行为有着天壤之别。当今世界知识产权法的最激进最坚定的布道者——美国自身的发展历史清楚地显示这一道德诉求的虚伪性:一百年前的美国在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产权“海盗”呢。[160] 历史告诉我们,分享他人智力成果,并不像西方所宣扬的那样伴随着强烈的道德内疚感。中国的法院应该正视这一历史事实,将“社会公众对信息的自由交流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加以珍视” [161]。
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对所谓的“劳动者控制劳动成果”法律原则作严格限制的解释。 “财产权源自法律的创设,并不源自价值——哪怕这一价值是可以交换的。”[162] “一个产品耗费生产者金钱和劳动,他人愿意支付一定的对价来购买,并不能保证它能够获得财产权”、“从法律上讲,并不能因为竞争者不劳而获,牺牲了对手的利益就是不正当的。” [163]在知识产权法成文法之外, 劳动者控制其智力劳动成果这一原则仅仅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劳动者仅仅对处于保密状态的智力成果享有控制权。一旦劳动者决定对社会公开其劳动成果,比如出版其作品、公布其技术方案、销售特定设计的商品等等,则劳动者就丧失了对此类智力成果的实际控制权。社会可以象利用空气和阳光那样分享此类智力成果。[164] 只有依据知识产权法的明确规定,才能对这种自由利用进行限制。英美法的法官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165]在中国知识产权领域,我们同样有足够的理由拒绝接受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传统, 拒绝承认劳动者对其智力成果享有当然的支配权。法院在适用民法通则、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时,不能认为“劳动者对其智力劳动成果现有支配权”是中国社会的诚实信用原则、商业道德的内在要求。
(二) 限制原则条款的兜底适用
中国司法和理论界,关于不正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有着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在法律的适用上,知识产权法的规定优于不正当竞争法,它们之间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 [166] 在这种观念指引下,如果权利人在知识产权法上无法获得救济,那么法院依然可以利用不正当竞争法的兜底适用来提供替代保护。不正当竞争法的兜底适用为法官造法提供了理论上的借口:在成文法中找不到法官期待的答案,法官不认真思考找不到答案的真正原因,就选择原则条款进行造法。[167]要避免法官肆意造法,就必须从制度上明确知识产权法和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条款之间的关系,消除模糊的兜底论的借口。
首先,应当明确知识产权法部门法在各自保护领域的独占适用。各个部门法的适用领域是以其保护客体的外在形式来划分的。比如,只要某潜在的保护客体具备了作品的外在形式要件,则所有与该客体有关的利益的保护,均独占性地适用版权法。[168]此类客体具备了成文法保护客体的形式要件,就推定为落入成文法立法者的视野,因此立法者必然要对与此类客体有关的各类利益的保护做出了政策上的取舍。在没有明确的例外规定时,无论知识产权部门法对此类利益的保护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法院均应接受这一结论,不得在部门法之外进行新的造法尝试,否则将违背立法政策。[169]前文提到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未注册商标、未采取保密的非专利技术等等,都分别具备了版权法、商标法、专利法上保护客体的形式要件,这时就应当维护各个部门法对各自客体的独占适用。即使知识产权法最终以不符合某些法定要件为由拒绝保护,[170]法院也不能再利用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为这些客体提供所谓的兜底保护。
其次,应当维持既有知识产权权能体系的刚性,限制法官利用知识产权法或者其它法律的原则条款在既有的权利束之外创设新的保护权能。如前所述,如果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已经为某些客体提供了保护,那就意味着立法者已经在现有的法律所创设的权能体系下确立了一种利益平衡关系。法院不应在知识产权法、民法或者其它法律的原则条款的名义下,在现有知识产权法的权能之外创设新的权能,打破立法者确立的利益平衡关系。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反向假冒、信息网络传输权等案件中,[171]中国的法院显然超出了现有商标法、版权法的框架,为权利人创设新的权能。
本文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法官在任何情况下适用民法或者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社会进步的确有可能带来一些完全超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立法者预期的新问题,如果法院不利用原则条款为这些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将危及某些社会公众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智力成果的供给,则法院可能需要考虑利用原则条款进行扩充解释为当事人提供适当的保护。即便如此,法院也要坚持以功利主义指导司法活动:知识产权法没有作具体的设权性规定,则应初步推定该相关的智力成果处在公共领域,社会公众和竞争对手可以自由取用。法院优先考虑的不是个案的创造者或者投资者如何最大限度地收回投资,而是如何维持知识产权法所创设的公共领域的开放。只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不对创造者提供基本的保护,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市场失败并最终损害社会公众利益时,法院才可以考虑适用原则条款提供适当的救济。
(三) 谨慎对待市场失败论
人们为一种超出现有知识产权法范围的新客体的保护进行辩护时,最常利用的策略就是强调法律保护与正常供给之间的必然联系,宣称没有保护投资人对该市场价值的控制,将不再有人愿意投资于相关领域向社会提供该智力产品从而导致市场失败。实际上,在很多领域这一说法并不可靠,仅仅是权利人游说司法机关的堂皇借口。[Page][172]比如,在数据库保护方面,美国的实际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在Feist案之前,美国版权法对数据库的保护就非常有限,却没有多少人向国会抱怨当时的保护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创造动机。[173]在最高法院宣判Feist案前夕,美国数据库行业的发言人警告说,如果数据库得不到保护,该行业将崩溃,而且公众将难以获得高质量的作品。 [174]Feist案拒绝提供保护之后,数据库行业各种危言耸听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175]
数据库保护的例子说明,激励创造者提供一项新的智力成果的机制很多,赋予产权或者限制竞争对手搭便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176]在很多场合,市场上的领先时间就足以保证投资者回收投资成本赚取利润,从而避免市场失败。市场领先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复制过程的复杂程度、产品的安全测试、生产线的建立、市场的开拓等等。[177] 在特定的场合,这一市场领先时间机制可能足以保证创新者收回成本并获得丰厚的回报,模仿者对创新者的市场利益虽然造成一定影响,但并不足以威胁到创新者的积极性。[178] 在广西电视节目表案中,实际上法院就忽略了市场本身的机制。电视台制作电视节目表旨在推广节目提高收视率,即使没有产权保护,也不会对电视台的创作积极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79]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涉及作品标题(没有原创性)、作品角色形象、产品装潢等保护问题的案例。[180]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不保护作品标题和普通产品包装,不禁止作品形象的商业化利用(当然以不损害现有知识产权为前提),会对作品的供给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既然不保护智力成果与市场失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在适用原则条款造法之前,法院就应当要求原告证明市场失败将不可避免地存在。[181] 原告在相关智力产品市场上的利益减损的事实并不等于市场失败。原告必须证明:如果法院不提供救济,整个市场上该类智力产品的供给将难以为继,从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在没有切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律默认的规则是自由竞争符合公众的利益。
在市场失败的确存在时,法院给权利人提供的救济也应该仅仅限制在能够避免该市场失败的范围内。具体来说,法院需要考虑如下因素:保护的期限、保护的范围、是否适用禁令救济及适用的条件等等。[182] 要求法官依据非常抽象的原则条款,在个案中考虑这些因素肯定具有很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一些国家试图在立法中为此类造法活动制定指导性的规则,但是效果并不为学者们所认同。[183] 中国的立法者在短期内也不太可能改变这一现状。因此又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强调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尽可能避免法官造法。
六、结论
中国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利用民法或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条款,增加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扩充知识产权的权能,甚至直接否定成文法的规则,损害了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政策,破坏了知识产权法所建立起来的利益平衡机制。司法造法活动也损害了中国知识产权法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妨碍公共领域的行动自由。同时,司法活动对法律原则条款的宽松解释,也为外国权利人在中国寻求变相的知识产权保护打开后门,威胁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刻意维护的国际产业竞争的立法政策。
法官造法活动泛滥的深层次原因是部分法院接受所谓的劳动自然权学说的指导,在劳动者控制其成果的原则下,产生过度保护的自然倾向。实际上,中国立法者实际上选择了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社会公众也普遍对知识产权保护持现实的功利主义态度。本文认为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应该明确放弃所谓的个人本位的自然权学说的指导,坚持立法者所选择社会本位的功利主义立法思想。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法院应该坚持知识产权法的独占适用,只要相关的客体符合知识产权客体的形式要件,就应当排除知识产权法部门法以外的法律原则条款的适用,从而保证立法者所确立的立法政策得到贯彻。在新的完全超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立法者预期的新问题出现时,法院不得已适用原则条款也应当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要求知识产品提供者证明市场失败存在,然后法院才能够给予适度保护。
A Criticism of Judge-made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bstract:Some courts in
Key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 Numerus Clausus, Judge-made Law, Natural Rights, Utilitarianism
[1]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40页。
[3] 参见杨玉熹:《论物权法定主义》,载《比较法研究 》2002年第1期,第35-36页。
[4] 王利明:《物权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11] Marybeth Peters,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Cour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H.R. 2652 105th Congress, 1st Session, Oct. 23, 1997, http://www.house.gov/judiciary/41112.htm。 又如H.R. Rep. No. 105-525, at 9 (1998) 也宣称特殊保护法案不创设类似版权的财产权,而是提供一种反对占用的侵权救济。转引自William Patry ,同注7,第396页。
[16] 莒县酒厂诉文登酿酒厂,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第3期。
[17] 韦之,同注9,第31页。姚欢庆:《莒县酒厂诉文登酿酒厂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评点)》 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9956 (
[18]广西广播电视报社诉广西煤矿工人报社案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年第1期。
[19] 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中没有直接表述,引自孟勤国:《也论电视节目预告表的法律保护与利益平衡》,载《法学研究》 第18卷 第2期 第152页。
[21] 张平:《中美数据库著作权保护的司法比较》,载《知识产权》, 1998年第5期, 第5页。
[23]美国微软公司诉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案((1999)一中知初字第182号)案中,法院就不认为域名本身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
[25]参见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
[28] 参见《商标法》(2001年修订)第13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
[32] 北京仪表机床厂诉北京汉威机电有限公司案(北京(1995)一中知初字第54号),孙建、罗东川主编:《知识产权名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年版, 第265-270页。
[35]杨金琪编著:《最新知识产权案例精粹与处理指南》,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第659-660页。
[37]北京市京工服装工业集团服装一厂诉北京百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等,北京市(1994)中经知初字第556号。
[39] 北京市京工服装工业集团服装一厂诉北京百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案的法院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这应该是判决通篇没有提到商标法的原因。同注37。
[40]法院的判决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九)项、第(十)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
[41]王蒙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案 北京(1999)海知初字第57号。
[4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第三条。
[44] 张承志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1期,第28页。
[46] 《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17条、第13条。
[58] 吉米·边沁(Jeremy Bentham): 《立法理论》( The Theory of Legislation),李贵方等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138-140页。
[61] Ronald V. Bettic , 同注60,第25页。
[70] J. W. Harris, Property and Justice, Clarendon Press,
[71] 参见 1960年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 载周林、李明山等 同注68,第321-324页。
[77]中国版权的诸多历史文献可以参见周林、李明山等,同注68。
[79] H.R. Rep. No. 2222, 60th Cong. , 2d Sess. 7. (1909) 转引自Paul Goldstein, 同注78,第1:36页。
[80] 许超:《软件最终用户侵权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载《电子知识产权》,2002年第9期,第37-38页。
[81] 关于这场争论,可以参考博客中国网的“我反对——争论《软件保护条例》”专题。该专题将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对软件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问题的规定视为民间抗议的胜利成果。参见http://www.blogchina.com/idea/call/。
[83] Justin Hughes, 同注48,第141-152页。
[8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条;作为对比,《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并没要求著作财产权中止后继续提供精神权保护。
[87]江平、苏号朋,同注86,第51;曹诗权等,同注86,第33页。
[88] Charles R. McMani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West Publishing Co., 1991, p.9.
[92] Douglas G. Baird, 同注89,第414页。
[93] Charles R. McManis, 同注88 第9页。
[94] 参见Maya Alexandri,同注7,第 335-336;William Patry ,同注7,第P382 ;Douglas G. Baird, 同注89,第414页。
[95] 王利明:我国民法的基本性质探讨 浙江社会科学 2004年第1期 第110;同样观点参见江平、苏号朋, 同注86,第51;曹诗权等,同注86,第27-36页。
[96]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 Serv. Co., 499
[98]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 Serv. Co., 499
[100]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 Serv. Co., 499
[101]北京阳光数据公司诉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案,案例参见孙建等,同注22,第262页。
[102] 关于数据库特殊保护立法的介绍,参见崔国斌:《数据库保护的立法现状与理论基础》,载《北大知识产权评论》,2002年 第一卷,第90-110页。
[104] 1996年外交会议上WIPO的数据库公约(WIPO Database Treaty)没有获得通过。参见WIPO,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Databases, Dec. 20, 1996,http://www.wipo.int/documents/en/diplconf/distrib/100dc.htm (
[105]参见董葆霖:《商标法律详解》,中国工商出版社 2004年版,第15-16页。
[106] 比如,北京市东城区景山炉灶曹维修服务部诉北京育德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案(一审),案情介绍参见罗东川等, 同注30 ,第287-294页。
[107] 如前所述北京仪表机床厂诉北京汉威机电有限公司案一审判决(同注32);宋维河诉东北菜风味饺子馆不正当竞争一案(同注36)等。
[108]参见Bonito Boats, Inc. v. Thunder Craft Boats, Inc. 489
[109] Douglas G. Baird, 同注89,第425页。
[110] William Patry ,同注7,第383页。
[111] Lloyd L. Weinreb,Copyright For Functional Expression,111 Harv. L. Rev. 1253, 1181(1998).
[113] Bonito Boats, Inc. v. Thunder Craft Boats, Inc. 489
[115] 法院在判决时参考了WIPO的新版权公约WCT。参见蒋志培、张辉:《依法加强对网络情况下著作权的司法保护》,载《人民司法》,2001年第2期,第10页。
[116] 比如,金勇军:《好一个‘等’字了得!——评张承志诉世纪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793,(
[117] 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或者共同侵权责任,参见蒋志培:《网络联线服务者著作权法律责任》,载《电子知识产权》,1999年第11期,第14页。
[118] 中国立法者技术上对所谓等、“其他权利”的滥用,显然也从客观上对法院的造法活动提供了帮助作用。不过,这不是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
[119]北京市京工服装工业集团服装一厂诉北京百盛轻工发展有限公司等,同注37。
[120] 《商标法》(1993年修订)第38条第(1)款。
[121] 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321页。
[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01年修订)》第五十一条规定第四款。
[123] 国内的食品、酒类、药品、电子、化工等诸多行业都存在普遍的分装业务。很多企业就是通过分装业务建立自己的品牌。按照鳄鱼反向假冒案的判决,这些行为的合法性都或多或少要受到质疑。
[126] 比如欧洲数据库保护指令(EU Directive on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所确定的保护模式。相关介绍参见崔国斌,同注102,第93-94页。
[127]广西广播电视报社诉广西煤矿工人报社案,同注18;北京阳光数据公司诉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案,案例参见孙建等,同注22,第262页。
[133]参见Douglas G. Baird, 同注89,第414页。
[134]这一原则条款一旦被扩张利用,几乎可以涵盖一切智力活动成果,具体介绍参见韦之,同注9,第31-32页。
[136] 比如在北京市东城区景山炉灶曹维修服务部诉北京育德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案中一审与二审的意见对在先权的理解就完全对立。案情参见罗东川等 同注30 ,第287-294页。
[139] Lloyd L. Weinreb,同注111,第1181页。
[140] Wendy Gordon, 同注53,第280-281页。
[141] Miguel Deutch,同注125,第523页。
[143] 参见《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2条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3条。
[146]参见吴家柱:《我国数据库产业发展对策研究》,载《情报学报》,1996年06期,第41页。
[147]邹汴:《论数据库的保护》, 载《电子知识产权》,1997年第1期。类似观点参见张平 同注21,第3页。
[153] 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内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就足以说明功利主义的财产观并不与财产权神圣的观念誓不两立。
[154]自然权学说的方法很容易从劳动转向产权,即便在美国,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权学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促使很多偏离正轨的判决得以出台。参见Wendy Gordon, 同注53,第192页。
[155] Lloyd L. Weinreb, 同注111,第1219页。
[156] Edwin C. Hettinger, 同注55,第22页。
[161] Edwin C. Hettinger, 同注55,第20页。
[162] International News Serv. v. Associated Press, 248
[164] 参见Paul Goldstein, 同注78,第1:31;William Patry,同注7,第382;Douglas G. Baird, 同注89,第411页。
[170] 比如,作品的原创性、发明的三性、强制注册要求等等。
[172] Lloyd L. Weinreb, 同注111,第1236页。
[173] William Patry, 同注7,第386页。
[174] Lloyd L. Weinreb, 同注111,第1236页。
[176]对智力劳动者的回报方式,除了财产权激励外,还可以是其他的费用、奖金、致谢、表扬、安全保障、社会地位、权力等方式。参见Edwin C. Hettinger, 同注55,第25页。
[177] Dennis S. Karjala ,同注7,第2602页。
[178] 有关市场自然领先时间(Natural Lead Time)与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深入讨论,参见J.H. Reichman, 同注6。
[179] 现在国内央视、凤凰等主要的电视台都在其网站、电视频道中发布节目预告甚至节目广告,即是明证。
[180]作品标题有关的案件如:郭石夫诉娃哈哈公司案(上海(1998)沪二中知初字第5号)、季康诉曲靖卷烟厂(“五朵金花”)案,相关评论参见孙玉锋、胡海燕:《<五朵金花>:作品标题应适用著作权法保护》,载《人民法院报》,
[181] Dennis S. Karjala, 同注7,第2607页。
[182] Dennis S. Karjala, 同注7,第2604页。
- 个人简介:(学术)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
- 邮箱:fengxiaoqingipr@sina.com
-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
- 个人简介:(实务)
- 最高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 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首届研究员
- 中欧仲裁中心仲裁员
- 深圳、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 中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 中国审判研究会知识产权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 通讯处:(Zip:100088)
点击进入免费咨询>>